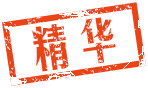- UID
- 78618
- 积分
- 5829
- 威望
- 268
- 桐币
- 2466
- 激情
- 16708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238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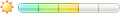
版主
  
- 积分
- 5829
 鲜花( 89)  鸡蛋( 1)
|
一
常常地,小屋里除了我,就是笛。
静静地对着窗外的,是早生华发的我;寂寞地挂在墙上的,是褐红色的笛。
当我的目光投向笛,笛那圆润修长的身子便泛出一线光亮,像它感应到我的心灵而睁开了双眼——实际上,那只是窗外光线的反光;且随着我的走近,或上或下的,或左或右的,闪动不已,像一个聪慧的少女,在说话之前,为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而机敏地眨动双眼——其实,也只因为我的视角在变化。
当我将笛取下,笛的身子便由冷硬而趋温软,似因我的体温而得以复活;当我将笛凑近嘴边,笛又如一个踮着脚尖闭上双眼送上红唇的清纯少女,要把自己的美丽整个地融入我的生命。
在我的气息中,笛不再沉默,像一个氧原子遇上两个氢原子,一种清亮的东西从笛孔流出,溢满整个小屋之后,又透过墙壁,踏着花瓣草尖,随河流而远,为清风弥散,氤氲在盛满鸟语花香的湛蓝天空。
当笛声停歇,巨大的宁静合拢而来,如一道飞瀑,涤去我心中的所有欲念,在清明之中,在小屋之外,总有一种东西,如人类发向太空寻找外星文明的电波,在月亮之上,在宇宙之间,不倦地漂泊追寻……
二
小时侯,我痴迷笛声。每当收音机或电影里有笛声响起,我就会屏住呼吸,紧起耳廓,惟恐漏听一个音节,影幕上那横笛伫立的剪影,笛声浸润的月夜……总要在我的心中反复低回。那时的我尽管不曾见过笛,却当笛声是世上最动人的声音,而把吹笛看作是最美妙的事,甚至以为一切美好都会随笛声而来。
第一次见到笛,是在父亲的抽屉中。那时,父亲在县医院住院,母亲跟去照看他,家中只有宠爱我的奶奶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就为满足一时膨胀的好奇心,我撬开了父亲的抽屉,一支小巧悦目的黄色短笛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发现让我不胜惊喜: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居然就在我的身边!尽管当时我好紧张,之后还有后怕,好长一段时间因担心父亲发觉而忐忑不安。
父亲病逝后,这支短笛就理所当然地归我所有。从此,一有余暇,我就练习吹笛。
一开始,我吹出的笛声难听无比,母亲一听到我的笛声就格外生气,怨我不好好读书不争气,当我是仇人一样恶狠狠地骂。
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有了不止一支笛,除了父亲的那支,还有两支。
一支是我在学校借的,这是一支当时我能见到的最好的笛,苏州乐器制造厂制造,颜色跟父亲的那支相像,由两截相接,看上去很精致,吹出的声音明亮悦耳。我选的是那套笛子当中调子最高的E调笛,那时的我喜欢那种能传得很远的笛声。
另一支不知谁送的,就端端正正地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也没留个纸条什么的加以说明。笛身是褐红色的,显得要艳丽,笛管要粗,调子要低,笛声低沉而响亮。如果说高音笛适合在热闹的场合吹,那这低音笛则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吹,因为它的声音接近于箫,但比箫声响亮。我喜欢把它挂在墙上,作为房间的一样装饰,表明我对它的喜爱,同时也想弄清楚送笛的是谁。然而,一直到现在,这还是个谜。
那时,我已能将笛声吹得流畅悦耳如行云流水了。我还练出了这样一种本领:无须记谱,凭感觉就能吹出我会哼唱的所有曲调。
在家里,逢到我吹笛时,母亲不仅没了从前的粗暴,反而格外温柔体贴,连从我身边走过的步子也放得很轻很轻,似乎就怕惊扰了我……就因为我不再是学生或孩子了吗?
在学校,多少个中午,当学生在校园里快乐地奔跑,我奏出欢快或抒情的笛声,像他们身边的清风,把他们相伴;多少个黄昏,我放飞我的笛声在寂寞的校园,如孤独的黑蝙蝠,划一道道不甘心的弧线;多少个夜晚,我的笛声又伴着虫吟,成猫头鹰那不能被黑暗湮没的眼,亮着一份对感情的执着;多少个日子啊,我将我的热情与梦想寄寓在笛声,我把笛当作一支射向希望射向成功的生命之箭,也当作倾吐心声追求爱情的一件工具……
也曾有人远远地驻足倾听,也曾有人来到我的窗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冒冒失失地推开我的房门,像狐仙一样顽皮地跳进来,打断我的笛声,让我注意她那比阳光更可爱的笑脸,让我以为我可以放下笛,去拥抱真正的爱情了。
最终,除了一支笛,我的手中并没有增加更多的真实,反而凭添一种空虚。
我终于醒觉:动听的笛声旁边未必就有美好的事物相伴!
三
我依然吹笛,尽管我不再青春年少,不再心存奢望。在吹笛的过程中,我有时将自我一分为二:一个是忘情吹笛的我,一个是倾听笛声的我。这样一来,我既可当笛是我的另一副还不曾喑哑且要含蓄优美的嗓子,使我的生命不至于无声无息,又可让我随自己的笛声穿墙而去,领略一种心灵的自由。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我,写我常常携笛上山,以证明我的与众不同,因为他认为,携笛上山当是还笛于自然,是一桩等同于放笼鸟于天空的雅举,而山中弄笛,更有伯牙抚琴觅知音的况味。
但这是他的臆断而非事实。事实上,我常常上山,却从不携笛。在寂静的山岗之上,笛于我纯属多余,我尽可以将山上山下的声音当成音乐倾听,山上的声音自然是清幽美好的;山下那些平日听起来难以忍受的嘈杂声音,一到山岗,也像被洗净或过滤了一般,不乏美感。
实际上,对于大自然来说:笛何尝不是一截没有根茎或枝叶的残躯,一件附着了人的俗气而失却了自然气息的竹的标本!况且,大自然的天籁之声又岂是笛声可比的呢?真要携笛上山,笛不会羞惭,我却一定会的,我怕那些虫儿鸟儿要笑话我。
当然,作为我在俗世中的良伴和知己,笛对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它是我在滚滚红尘中联络自然的一个使者,我一天出不了红尘,一天便离不开它。每当黄昏来临,不开心的往事像夜色一样从窗外拢来,无人倾吐的我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笛,让自己与笛合二为一,去找寻那没有烦恼的乐土。
也只有笛那极富穿透力的声音,可载我一回又一回地远离尘世,重返自然。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