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31724
- 积分
- 122
- 威望
- 56
- 桐币
- 63
- 激情
- 25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9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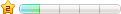
文都秀才

- 积分
- 122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12-3-2 13:28: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合食同住
相继戴有“淑勒贝勒”、“聪睿恭敬汗”、“英明汗”桂冠的努尔哈赤,一向是聪明睿智敏捷,想出了许多奇计妙策,解决了很多麻烦问题,越过了重重难关。但是,进人辽沈以后,他志得意满,骄傲自负,闭目塞听,误认为自己真的是奉天承运之君,所作所为,皆系顺天意,合民情,绝对正确,因而遇有挫折,便不冷静,不是反省思过,纠错革弊,而是大发雷霆,埋怨对方,胡干蛮干,做了不少蠢事。强迫辽东汉民与女真合住同食,就是一件笨拙之极的蠢事。
两个不同民族的人员,而且一个是征服者战胜者,另一个是被统治者战败者,要住在一间房,同桌吃饭,不是暂时性的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三年若干年,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古怪稀奇的事例。想出这个绝招,推行这项政策的,不是别人,而是素以聪睿著名和自负的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努尔哈赤就下命令,将建州地区女真陆续迁人辽沈地区。十一月初一日,建州地区女真的第一木昆(族)到达辽阳,到十二月初十日,后面的女真也都到了。
这样多的女真进人辽沈,自然需要解决吃穿日用和耕田住房问题。当时,辽民大批逃人关内,遗下大量田地房宅和耕牛粮食用具,只要调度适当,是能够安排好的。可是,努尔哈赤却用女真与尼堪(汉人)合住同食的方法来解决此事,犯了一个大错误。
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下达汗谕,规定了女真、尼堪要同吃共住。他说:
原曾令女真、尼堪合居一村,合食粮谷,合以草料饲马,女真勿得欺凌尼堪,勿夺尼堪之任何物品,勿掳掠,若如斯掳掠侵害,尼堪来诉之后,定罪。尔等尼堪亦勿伪作谎言,若伪造虚伪之事,令当事者双方面质而审理。审理之时,若有虚伪,则从重治罪矣。女真、尼堪,皆系汗之民矣。汗之金口教谕女真、尼堪皆合议公正为生,如若不听,违谕犯罪,则将重罪矣。女真、尼堪不得浪费或买卖粮食,若发现其有买卖者,则必治罪。若开粮窖,女真、尼堪合开。一个月,以尼堪之升量之,尼堪、女真一口各给汉斗四斗。
这道汗谕之中所说女真、尼堪“合居一村”,不准确,应是合居一屋,这在三个多月以后的另一道汗谕,表述得非常清楚。天命七年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又下了一道着重讲女真、汉人合住同食的汗谕说:
曾令女真、尼堪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今闻女真人令同居之尼堪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该尼堪岂给尔为奴耶?只因由故地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后,女真、尼堪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以外,女真、尼堪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女真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尼堪,则尼堪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尼堪人亦不可因降此谕,而肆意诬枉女真人。尔等皆为一汗之民也。
这就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女真、汉民合住同食一起耕田的奇怪政策。这项政策的实质,就是要汉民供养女真。当时,农村中,最主要的财产,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耕田、房宅、粮食和耕牛。按照汗谕的规定,村民的房屋所有权,受到严重的侵犯,他必须将房屋腾出来,让女真住,并且很可能是女真要占据好房,要占住大多数房屋,因为他是胜利者征服者,是真正的主子,而汉民仅仅是宽免不杀、有而为奴、汗所“豢养”的小人。村民对自己辛苦耕耘收获的粮食也失去了所有权,无权分配,无权出卖。收藏粮食的谷窖,是锁着的,开时,要女真、尼堪同开,不让汉民单独开。窖中的粮食,女真、尼堪同食,每月一口四斗,多余的粮谷,不许浪费,不许出卖,违令治罪。这些粮食哪里能说成是村民的粮食,他有什么支配权?可以肯定地说,这项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规定,就是基本上剥夺了汉民自己的土地、房宅、粮食、耕牛的所有权,就是让汉民供养女真,就是使女真成为汉民之主子。
事实上,女真官将和凶横诸申,确实是把同住的汉民看成是他们的阿哈,欺压汉民,抢夺财物,役使汉民为己干活,使用汉民耕牛,甚至侮辱汉民的妻子女儿,等等不法行为,难以枚数。努尔哈赤自己也知道这些弊病,在上面曾经引录的汗谕中,承认有女真使用同居汉民的牛车,令汉民运送粮草以及勒索财物的行为。
历史实际证明,努尔哈赤独创的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异常荒唐的,它严重地侵犯了汉民利益,加深了辽东汉民的灾难,破坏了农业生产,加剧了动荡局面,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加深了金国统治的危机。
(四)尽捕“无谷之人”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金国发生了又一件古今罕见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暴行,这就是号称英明无比的金国汗努尔哈赤,在半月之内,连下多次汗谕,责令八旗官将在辖区内清查和擒捕“无谷之人”,干了又一件极大的蠢事和坏事。
面对广大辽民反对金国汗、贝勒、八旗官将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努尔哈赤恼羞成怒,迷信武力,采取了更为野蛮的高压政策,在金国辖区内大肆清查和追捕“无谷之人”。《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十一对此事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记载:
天命九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遣派八旗大臣,前往赫扯木等地,查量汉民粮谷。督堂在致英额等地查量粮谷的大臣的文书中,传达汗谕说:
奉汗谕:赴英额、赫扯木、穆溪、玛尔墩、扎库木、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著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女真斗六七斗者,准其居住。一口有五斗者,或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核计若可以生活,则准其居住之。计之不敷者,则计入无谷之人数内。并将无谷之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
同日,对前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督堂告以汗谕说:
奉汗谕;著五牛录额真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女真斗六七斗者,令该户启程,遣之,给以田宅。一口有五斗者,及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合计可以维生者,则计入有粮之人数内,以遣其户。计之不敷者,则一汁入无谷之人数内。无谷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之粮谷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女真看守粮谷,倘失一石,即以该大臣罪之。勿剥人棉袍,勿以粮饲马。于盖州种棉及看守果木之汉人,令留三千二百名男丁。令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等城周围十里、十五里内之有谷之人,入城留之。
过了半个月,三月二十日,每旗增派15位大臣“前往量粮地方”,“命其尽行办完”,又下汗谕,布置工作,修改划分有谷无谷标准。汗谕说:
著将有谷之人之男丁数、人口数、谷数,造册报来。其粮谷由量主看守。迁来之户,给以女真之粮。令女真往取其粮食之。被杀之人之谷,乃库粮也,将其粮数,另行造册报来,由守粮之主一并守之。被杀人之财产、牲畜及什物,皆造册带来。勿解取被杀人妇孺所服之衣,无论其好坏,仍服原衣带来。一口有五斗谷者,即列入有谷之人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谷之人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谷之人。
第二天,督堂下书,命查明与女真同住之汉人粮谷说:“奉汗谕:与女真同居之汉人,一口有谷五斗者,则计人有谷之人数内。一口有谷四斗三斗者,若有牛驴,亦计人有谷之人数内,若无有牛驴,则取其户为奴。”
根据《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结合其他文献,对于这次清查、捕捉“无谷之人”,我们可以得出五点结论。第一,所谓“无谷之人”,是穷苦汉民,而“有谷之人”,则大都是比较富裕的有产之汉人。乍一看来,每人有谷女真斗5斗,折合汉斗为9斗,似乎不多,不宜作为比较富裕之人的标准,但在当时辽东条件下,一人有谷9斗以上,确很难得。辽东地区,连年战争,兵荒马乱,民不宁居,耕种艰难,灾荒频仍,年年歉收,谷价“踊贵”。早在辽阳、沈阳失守前一年(明泰昌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八月,辽东地区已是一石米价银4两,一石粟2两,这还是小斗,一石不及山东4斗,如按山东斗计算,一石米的价银当在10两以上,比诸正常年成,粮价涨了十几倍。粮少价昂,穷苦农民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很多人饥饿至死。《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五十四载称,“南方之人……饥饿而死者甚多”。
金国汗、贝勒虽然尽力搜刮粮食,以供军用,但仍然不能解决粮荒问题,连对作为巩固金国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来归蒙古人,每2口也只发谷女真斗1斗,可见粮食是何等的紧张。
这些情况表明,辽东地区的汉民,每人有女真斗谷5斗以上足以维生的人是不多的,而“无谷之人”则不在少数。
第二,这次查量粮谷的地区范围很广。这从三道汗谕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月初五日,督堂对前往“英额、赫扯木、穆溪、玛尔墩、扎库木、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传达了汗谕,从音额、赫扯木、玛尔墩到扎库木,这五处都是原来女真耕种居住的地区,可见,这些大臣查量的地方很宽广,包括了从抚顺、铁岭起,往东北延伸到原来女真处的广大地区。传达另一道汗谕,是告诉前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盖州以西,包括熊岳、复州等地,威宁营以东,包括奉集堡、清河、马根丹等大片地区。正月二十一日的汗谕,是要大臣查量“与女真合居之汉人”,女真与汉民合居的地区很宽广,以辽阳、沈阳为中心,包括海州、鞍山、盖州等州县。由此可见,在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都进行了查量汉民粮谷的活动。
第三,这次查量谷物,金国汗、贝勒花了很大力气,十分重视。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十、六十一的记载,从正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一日,半个月内,努尔哈赤接连9次下达查量汉民粮谷的命令,对一件事,下如此多的谕令,是很少有的。除第一次派遣大量大臣兵士查量谷粮以外,又两次增派人员,有一次竟派每固山各巧名大臣前往。命令之急,人员之多,花费力量之大,都是罕见的,可见金国汗对此事是何等的重视。
第四,清查“无谷之人”的原因,是为了遏制辽东汉民的反金斗争。努尔哈赤于天命九年正月十三日下谕说:“应视无谷之人为雌敌,彼等之中,有我何友?”
过了8天,正月二十一日,督堂下文书说:
奉汗谕:凡偷杀牛马者,火烧积谷、屯舍者,皆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欲由此处逃往彼地之光棍也。对于此等无谷闲行气食之光棍,无论女真、尼堪,一经发觉,即行捕之送来。若有妻、子,则将妻、子给与捕送之人。若无妻、子,则捉一人,赏银三两。因得辽东以后,尼堪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上怒而谕之。
文书所引的“汗谕”,有力地说明了辽东广大穷苦汉民猛烈反对金国汗、贝勒的压迫,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或是怠工,不耕田地,或是四处流浪,竭力摆脱金国的统治,或是秘密串连,与明联系,欲图逃人明国,或是火焚地主、金将的房宅粮谷,夺其牛马,武装反抗。并且,这种斗争,十分普遍,坚持不断,影响巨大,搞得金国统治者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视如眼中钉肉中刺,故下令严格清查。
第五,大杀“无谷之人”,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也是金国汗、贝勒消除反抗、武力镇压的“恩威并举”方针遭到重大失败的标志。就在汗谕指责无谷之人反金行动后的第六天,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选派人员前往各地,诛杀无粮之尼堪”。所有剥削者压迫者,都轻视穷苦百姓,历代统治者都采用各种借口,屠杀反抗他们的劳动人民,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是,像金国汗努尔哈赤这次仅仅以没有足够的粮谷不足维生为理由,就四处追查擒捕,大肆杀戮劳苦人民,还是极为罕见的。它必将激起汉民的更大愤怒,掀起更大的反金波涛。
(五)乙丑大屠杀
尽管金国汗、贝勒野蛮镇压武装起义,追拿逃亡的阿哈和尼堪,大肆捕杀“无谷之人”,但仍然无济于事,仅据《满文老档》的记载,5年之内(1621-1626年),比较大的起义与逃亡,就多达数十次。发生过反金行动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山由岩、暖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金国大多数辖区。辽民的反抗更加坚决,到天命十年(1625年),已经出现了震惊统治者的严重局面,努尔哈赤不得不特下急令,在汗宫门前专门设置报警锣板,规定报警信号。《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五载:
(五月初三日)汗曰:夜间有事来报,若系军务急讯,则击云板;若系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铜锣;若系喜事,则打鼓。
说完之后,“汗之门置云板、铜锣和鼓”。
《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报警信号规定的原因说:“时因粮荒,叛逃甚多,乱。”
所谓军务急讯,并不是明军来攻,当时明朝几遭惨败,危机四伏,根本无力派兵收复辽沈失地,而辽民反金斗争的蓬勃开展,即所谓“叛逃甚多,乱”,才是汗谕所说的军务急讯。可见,辽民的斗争,已经打乱了金国统治秩序,没法安宁,无力平定,形成了“乱”的严重局面,在金国最高统治者的门前,竟要赶紧设立报警装置,统治者已经睡不安枕了。
面临如此局势,努尔哈赤本应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反省,革除弊政,放松一点压迫,以收买人心,缓和矛盾,这才是解决难题的惟一办法。可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被辽民反金斗争气昏了头,大发雷霆,调遣八旗军队,在金国辖区内大规模地屠杀反金人员。
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历数汉民不忠,叛逃不止,命令八旗贝勒、大臣,带领兵士,分路前往,屠杀反金官民。他谕告群臣说:
我等常豢养尼堪,而尼堪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甄别屯中之尼堪。常言道,豹色好辨,人心难测。唯恐尔等听信奸巧之言,当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生员、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原注:正法即杀之)。为我等建城池、纳官赋之人,则建拖克索以养之。无妻挚独身之人,及应加豢养之人,则养之,赐以妻、衣、 牛、驴、粮谷,命编拖克索。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拒不从命者,亦予正法。自八贝勒之包衣拖克索之尼堪起,凡入女真家中之人,皆捕之,照例甄别。女真中之怪人、讨厌之人、顽固者,若说家中无有,或不知,而隐匿不举者,则罪之。明时非千总今经我委任为千总之人,一向居住沈阳,其父母家族皆来投者,则免之。家虽住沈阳,但未携父母,未带妻室,只以外妾假充居住之名者,不准居住。素未居住,因九月以来耀州、海州之消息,使其惊恐而来 沈阳之人,不准居住,照例甄别之。为恐在甄别时如以前一样,贿银而免之,故对沈阳、抚顺、开原、铁岭所属之人,比他处之人从宽甄别之。自广宁迁来之人,亦按抚顺、沈阳之人从宽甄别之。
在屠杀反金汉民时,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还颁行了指责辽民的告示。这道告示说:
我等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宅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虽如此恩养,竟成不足,(古河、复州等地叛逃不绝)……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女真而去,以及备办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国所遣之奸细,接受札付,备办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以前之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充役之人,知道什么?无 非为尔等之恶,受牵连而被杀耳。总之,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向明国,故杀尔等外乡之为首之人者,即为是也。小人筑城,奸细难容,即使逃亡,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
诸贝勒对众汉官训诫说:“众汉官,著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而使尔等脸面无光。”
八旗大臣遵奉汗谕,“分路前往,下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十三丁、牛七头编为一庄。”
《满文老档》编写者在记述此情后,又写道:“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后为天聪汗惜而止之,察所余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余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
虽然努尔哈赤文过饰非,巧言诡辩,力图将过失推与辽东汉民,声称系因辽民忘了不杀之恩,叛逃不绝,而大开杀戒,但诡辩终究掩盖不了事实,这次屠杀是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无人道的疯狂大屠杀。生员要杀;原为明国官员今为闲散者要杀;虽任千总但未久住沈阳者,或其父母妻子未同住沈阳者,也要甄别,其命难保;不该豢养者,要杀;“拒不从命者”,要杀。这样一来,就很难分清该杀不该杀的界限了,不管是官是民,只要领兵的贝勒、大臣不顺眼,认为你要叛逃,就杀,不需要什么证据。真是,杀,杀,杀,逢人便砍,见人就杀,搞得辽东天昏地暗,十室九空,也使得辽东以外其他明国辖地的汉人,闻之“肝胆俱丧”,切齿痛恨。
这次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人,清朝官书没有记述,但从生员之例,可以有些了解。明朝的科举学校制度规定:“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国学,即京师的国子监,又称太学。郡县之学为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大体上,府学有生员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在郡县地方,4卫以上,有军生80人。辽东是都司制,设卫而不设州县,辽东25卫中,有14所学校,即一个都司学和13个卫学。到了天启元年,即金军人驻辽东之时,辽东地区的生员,少说也有几千人,很可能有一二万人,但是经过屠杀后,除了早已逃入关内得以保全性命的生员外,辽阔的辽东地区,只剩下300余名生员,可见其杀人之多,诛戮之惨。
迷信武力的金国汗努尔哈赤和八旗贝勒,满以为经过这次大屠杀和编丁立庄,就可以把辽东汉民吓住,控制住,不再叛逃了,就可以安心地大举攻明,席卷全辽了,可是,事与愿违,辽东军民更加厌恶金国统治,“叛逃不止”,没有多久,强迫编隶拖克索的尼堪阿哈竟“逃亡殆尽”,连相当多的汉官都动摇了,也反对这样不分官民见人就杀的野蛮罪行,暗和明国秘密联系,待机反正,金国的统治更加不稳,也影响到一年以后的宁远之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