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74113
- 积分
- 312
- 威望
- 0
- 桐币
- 1
- 激情
- 358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81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1-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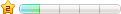
文都秀才

- 积分
- 312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12-5-3 16:53: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被捕
如果说反右是灾难的第一波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大饥荒就是灾难更大的洪流。目睹和亲身经历这些灾难的人,如果不是良知泯灭,或是迂腐得不可救药,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怀疑。但是,在当时,拔掉几个乱说话的右派分子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鸵鸟一般把头埋到沙堆里,试图明哲保身。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站出来说话不过徒招灾祸。经过这场反右,中国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被发配到穷塞旷野,惨遭凌辱与折磨,或一去不归,或被折磨得精气神尽丧,战战兢兢苦熬岁月。所以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面对铺天盖地的苦难,再也无人敢作异声,甚至连记录它的勇气都没有。林昭在初被打为右派的时候,曾经失眠、拒食,每日以泪洗面,甚至试图自杀。但没过多久,她就从个人的悲凄中摆脱出来,她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遇见了林昭,被林昭强行拉去吃饭。饭桌上,刘发清情绪低落,委靡不振,什么也吃不下。而林昭却有说有笑,吃的津津有味。她说,这不是个人命运问题,举国上下,都在反右,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灾难。“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但是她思考的又何止仅仅是一场反右斗争,她在思考先前的理想,整个中国共产革命革命的理想、现实和命运。她的心中,正在推翻十几年来一直热爱并忠诚的那些思想与事物。先前自己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是真理?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真理又是什么?反右运动给广大同胞、她的朋友和她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命运转折,只是促使她进一步深思的一把钥匙。
刘发清不久便被发配到甘肃劳改。
来到人大之后,她便被安排在人大新闻系书报资料室接受监督劳动,同在一起劳动的还有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以及另一名青年甘粹,主要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
甘粹部队出身,被保送到人大新闻系学习,他因为凑名额,也被打为右派。林昭体弱多病,甘粹对她多有照顾体贴。两人平时一块儿进进出出,又是青年男女,于是好事之徒们眼睛便亮了起来,这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又多了一个无聊的话题,说是林和甘在谈恋爱。交头接耳、窃笑、流言蜚语,总之是些很无聊可笑的行径。“组织上”也注意到这件事,于是找二人谈话,说是右派不能谈恋爱。这本是件子虚乌有的事,可是两人一听不干了,不是不让谈恋爱么,我们偏要谈给你们看看。于是弄假成真,两人真的谈起恋爱来。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弄假成真,他们应该互相都有好感,再加同病相怜,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只是火候未到。“组织上”的态度,反而促成了二人的关系,于是同出同进,毫无顾忌地拉手,经常手挽手在人民大学校园内招摇过市,在当时,这种做法可谓是“前卫”之极。
林昭喜欢甘粹而对张元勋却无所表示,大概女孩子们都很感性,切身的关怀和体贴更容易让她们感动,而那些胸怀理想者,她们只是将其当作志同道合的友人。
在这个时期,她写就了两首著名的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士受难日》。从这两首诗来看,她已经抛弃了过去的理想,认清了某些人的真面目,转而歌颂为人类光明和自由而受难的英雄。
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带甘粹去王府井教堂做礼拜,给没有任何基督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的故事,二人虽身为右派,为众人不耻,却其乐融融。到了五九年,两人决定结婚。然而结婚需要经过“组织”批准,再由校方开具的介绍信,拿着介绍信才能去登记。早在他俩谈恋爱时,“组织”上就强烈反对,又因为他们不顾“组织”的阻挠而相恋,领导们更加窝火,想结婚,门都没有。不仅如此,这个“组织”还决定拆散他们,九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农二师劳改营,一去就是二十二年,受尽地狱般的折磨。他为这段爱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想必后半生都是在悲哀与怨毒中度过。
恋人远流他乡,此去生死未卜,不知是否还有再见之日,哪个姑娘能不伤心欲绝?甘粹走后,林昭便病倒了,她的病是支气管扩张,到了冬天,整日咳血不止。于是提出回上海母亲身边养病,校方对此请求视而不见,只是一味拖延不允。
一九六零年初,病一日重似一日。但此时她的病情也传到了人大校长吴玉章那里,吴校长亲自批示,允许林昭返沪养病,接着,母亲许宪民来到北京,接走了林昭。
反右期间,兰州大学三十九名右派师生被发配到武山、天水两县农村劳改。这些右派学生虽深处政治和生活的漩涡之中,但理想依旧未曾破灭。在学校里,他们只是有些模糊的想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有些空谈空想。如今,到了农村,亲眼目睹了大饥荒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当时,一边是大饥荒,饿殍遍野,一边却是大放高产卫星,亩产动辄号称上万。为了应付检查团,农村干部发动农民,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庄稼都移植到一块地里,检查团看了以后心满意足地走了,第二天,这些被动了根的庄稼便再也栽不活了。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形促使这些年轻人更深地反思,成了真正的“右派”。历史系的学生张春元提议,办一份刊物,大家一致赞同,便开始筹办。刊物被定名为《星火》,他们深知办刊物的下场是自取灭亡,但他们义无反顾。
这些青年一次读到了《海鸥之歌》,深有感触,对诗的作者不禁充满了倾慕之情。真不知道这首诗是怎么传到他们那里的,当时没有互联网,但真理的呼声自然会传播开来。今天的互联网上,不知每天要湮没多少文字垃圾。
还是六零年,林昭在上海养病,经过医治和调养,她渐渐恢复了健康。这时,张春元和另一名兰大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从天水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只因慕林昭知名。他们和林昭谈了创办刊物的事,林昭为他们拟定了一份办刊的纲领草案,并把自己的长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日》交给他们,让他们发表在《星火》上。
这群学生办刊物没有经费,便自己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自己刻蜡版,印成了首期《星火》,八开纸,三十多页,先不能公开,仅在自己人中传阅。收录的文章中,有一篇一篇支持彭德怀为民请命(当时彭已经被打倒),抨击毛的倒行逆施。针对大饥荒的问题,有一篇文章认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直接恶果(这观点多么准确!),还认为共产党已经腐朽,应该再来一次革命(不能责怪他们留恋暴力,在当时的环境下,看不到非暴力抗争的希望。)。鉴于中国没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内部的同志,希望由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他们计划日後寄给各省市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
中文系女学生谭蝉雪,张春元的未婚妻,她是右派学生的头领。六零年春,她决定偷渡,争取外援。但没有偷渡成功,她被捕了。四、五月间,张春元和右派学生苗新久外出联络。苗新久归来了,张春元却一直没有消息。七月,张春元也被捕。右派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他们私刻兰大党委和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伪造介绍信,出门用的是假证件。当局花了两三个月才弄清他们身份,终于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当时,《星火》只出了第一期,第二期仍在编辑中。
这时,林昭的老朋友,在甘肃劳改的右派分子刘发清已经奄奄一息。口粮减到每月二十斤,没有任何菜和副食,刘发清和很多还在苟延残喘的难友一样,浑身浮肿,躺在床上不敢动弹,生怕损失每千分之一个卡路里。这病是饥饿所致,无药可治,只好听天由命,或者说是在等死。危难关头,他收到一封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上还附有一个小包。刘发清拆开小包看时,里面是一些粮票。他颤抖着一张一张取出那些粮票,都是五斤一张的全国粮票,共七张,刘发清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林昭在信上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刘发清就是靠着三十五斤粮票,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最后他终于活了下来。在给林昭的回信中,他鼓励林昭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去。他这样说,也许并非是不理解林昭,只是因为右派们的信件都要被拆开检查,发现有出格言论就要罪加一等,他也只好如此。后来又收到了一封林昭的来信,她说:“我于足下同舟人也,舟要靠岸吾亦可登。”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十月,参与《星火》杂志的三十多名兰大右派师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徐诚均十年以上。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杜映华是中共武山县委第三书记,受此案牵连被判刑五年。主犯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但他象那些传说中热爱自由的好汉一样,不久就越狱逃走了。
几乎同时,在苏州老家养病的林昭被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警察逮捕,罪名“现行反革命”。此前,她曾致信张元勋青岛老家,但当张元勋大哥复信告知弟弟的情况的时候,她已被捕。
抓捕林昭时,她父亲彭国彦恰好进来,老人(其实并不算老,不过已经憔悴)当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言毕踉跄离去。这位一生郁郁不得志的老人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无路可走,近年来,这位曾经的一县之长,曾经留洋到过联合王国的大学生,一直在家中靠糊火柴盒补贴家用。他年轻时曾有一番壮志,但很快被现实捻碎。于是他把家庭的希望寄托在能干的妻子身上,可妻子也无能为力。后来,他又寄希望于有才华的大女儿,如今大女儿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他意识到不久就将家破人亡,自己苟活在世上只是徒为亲人增加负担?一个月后,老人服鼠药自尽,当局称其为“畏罪自杀”。
四 囹圄中 上
在林昭的罪行材料上写着:“张(春元)回兰州前,林赠予一本现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及自己写的反动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日。’后张、顾参考此书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林的反动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火》刊物上 。”
被捕后,未经审判便先后被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上海第二看守所、上海静安分局看守所。入狱以后,她便开始写思想日记。狱方一度把她和一名叫俞以勒的基督徒关在一间囚室里,俞以勒被狱方认为是“顽固”,狱方希望两人信仰发生冲突,以至相互打击。但是,两人相处却十分融洽。林昭在俞以勒身上看到了基督徒信仰的坚韧、纯洁,并深为基督博大情怀所感染。在后来的岁月里,她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但基督的精神已经成为她精神支柱之一。
开头的一年多里,她在牢内音讯全无,母亲各方奔走也无济于事。后来,才渐渐有了信出来,可以带些钱和所需物品进去,但家人想和她见面很困难。家人都希望她在狱中不要生事,早日熬到刑满出来团聚,但每次得到她的消息,总是十分沮丧,因为她在里面“表现”很坏。每次通信,林昭都向家里要很多白床单,开初不明白她用来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她将那些白床单撕成条条写血书。她用发卡、竹签、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刺破皮肉,一点一点蘸着鲜血书写。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狱卒们是如何对待囚犯的。比如有一个女狱卒,曾被林昭蔑称为“不中用的警犬”,此人对待犯人非常残忍无情,林昭便与她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指责她对犯人实施惨无人道的虐待。让我们想象一下两个女人隔着牢狱的门窗相互攻击的时的情景:一个穷凶极恶,掌握着打杀大权;一个绝不屈服,虽身为阿其那(满语:板上冻鱼),却掌握着道义。两个女人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誓不两立,相互恨之入骨,想必怨气冲天,几近歇斯底里。
她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开始,她斗争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她几乎每天都给狱方找茬,她的名字在狱中变得响当当起来,一些狱卒看守对她恨得牙根痒痒。当着些人当班的时候,她便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难友劝她不要硬碰硬,鸡蛋碰不过石头。她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还留下了这样的日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看起来,她似乎有些狂燥,失去了女性温柔的一面。当我们分析她为什么要选择抗争已经这样的抗争方式的时候,在她的日记里,找到了她躁动不安的原因:“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实际上,她的这种抗争并不象她所说的那样乐观,亿万个鸡蛋砸上去,顽石同样巍然不动,更何况,到哪里去找亿万个鸡蛋呢?靠自己的努力在黑暗的牢狱里打出一道光明来?这是痴人说梦。况且,即便真的打出一道所谓的“光明”来,这光明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道主义方面有所改善,即便让你们吃饱了,犯人依旧是为万众所不齿的犯人,所有的国家机器,所有的舆论机器,都在开动马力,把耻辱倾泻在你们身上。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光明”。难道这些她就没有想过吗?也许想过,也许她真的就是那样的执着。此时的林昭,已经完全认清了专制者的真面目,已经不会为谎言所困,不再迷惘。她的抗争,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她要的是抗争本身,而不是抗争的结果,她想借此向那个庞大的专制机器表明:我决不屈服!
她的反抗行为自然招来了更为残酷的虐待,在这些虐待之下,她病情加重,咳血不止。一九六二年三月,狱方通知许宪民,将林昭接出监狱,保外就医。莫非狱方忽然发了善心?或者有大好人从中出力?大谬不然,因为当时张春元依旧在逃,当局想以林昭为饵,诱捕张春元。
母亲到狱中去接林昭,她不肯走,母亲拉她,她就把住监狱的桌子,坚决不肯走,还说:“你以为把我保出来吗?还要把我抓进去的,何必多此一举。我要坐穿牢底斗争到底。”她如此看重坐牢受难,是否是因为受了基督的影响?后来,母亲找了个力气大的人,强行把她抱走了。这种举动多少显得有些孩子气,然而支撑她在狱中漫漫岁月里承受那些非人苦难的,正是这一片赤子之心,以及女性特有的坚韧。
回家以后,家人追问她为何索要白床单,她支吾其词。母亲摞起她的袖子,发现上面斑斑点点的切口疤痕,登时痛哭流涕,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保外就医期间,她也没有闲着。七月,写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呼吁他以蔡元培为榜样,营救受难学生。这期间,她结识刚从江苏滨海劳改农场释放的右派分子黄政,黄政曾在劳改农场里专干掩埋尸首的活计,江苏乃富庶之地,但每天都有多名劳改人员饿死病死,状况令他惊心,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再不能这样下去,决心做点什么。黄政遂与林昭、朱泓等人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并联系到住在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请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据说,她还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狱中回忆录》,但这部回忆录一直未能面世。写这么多字的作品是件很辛苦事,她又在病中,在如此短时间内便做了这么多工作,可以想见她的艰难与执着。
后来林昭和黄政又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国改革方案,提出了八项主张,然而他们的活动早有人监视,十二月二十三日,林昭再次被捕入狱,黄政也随后被捕并判刑十五年。
张春元也被捕了,他重被关进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在此监狱服刑的杜映华被“释放”后,仍旧没有自由,而是在该监狱“就业”当了一名工人。六八年的时候(一说六**四年,但这年杜映华于六零年被捕,此时五年刑期未满,殊无提前释放的可能),张春元再次试图逃走,而且这次不是他一人逃走,而是串联其他犯人一起逃走,事败,张春元因“密谋暴动越狱”,被枪决于籍河岸边,一颗热爱自由的星辰陨落。同被处决的还有杜映华,他被指为张春元传递消息。
林昭被捕后投入臭名昭著的提篮桥监狱,这里是上海的巴士底、伦敦塔。未久,便开始了对她的审判,因“拒不认罪”,被重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连外国人的都知道,中国的审判不是法官说了算,而是“上面”的意思。
狱中的情景,著名记录片胡杰导演曾试图采访当年的狱卒之流,但都遭拒绝。这段历史,今天仍只能凭只言片语管窥一斑。
到了提篮桥,她依旧喊口号,唱革命歌曲,和狱卒们对着干。有一次狱中的伙食忽然少了,也没了两周一次的“改善生活”。于是她带头喊口号抗议,开始时,呼应者寥寥,她便唱起《国际歌》,难友们纷纷响应,歌声震动监狱。(可笑的是,今天,《国际歌》这首共产革命的战歌,共产党员的圣咏,已经被禁,理由是“与时代精神不符”。)
狱方从未见过如此顽固的犯人,以为是碰上了神经病,便送她去上海精神病医院做精神鉴定。由院长粟宗华亲自执行,粟院长也许是出于保护她的目的,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或者这位院长真的认为林昭精神有问题,反正今天中国的精神卫生事业仍十分落后,顶着高学历、高职称的庸医随处可见。更何况在当时?这些人,他们心中有一个“正常人”的模子,这个模子里的人,必是循规蹈矩,思维不越雷池半步。超出这个模子之外,便是异端精神病。就象契科夫小说《第六病房》那位医生。所以这一鉴定并不能当真。这位粟院长,文革期间饱受批判之苦,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林昭和严慰冰(陆定一太太),郁郁而终。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她被剥夺了纸笔,从此一门心思写血书。这些血书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有床单、衬衫、废纸,甚至墙上。到她被害的时候,共写了二十多万字,有各式各样的文章和诗歌。人类历史上,如此执着的壮举绝无仅有。
狱方当然不会放任她,他们声称:“不制服你这个黄毛丫头就不相信。”回击是这样的:“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他们采取种种残酷虐待的手段,单号子、铐子、棍子,各种手段纷纷跟上,不知还有没有老虎凳辣椒水。在林昭的一些日记片段中,记录了一些虐待情景:“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据以为曾经蹲过该监狱的人回忆,这些铐子的花样有“穿心铐”、“扁担铐”、“飞机铐”、“猪猡铐”、“吊铐”等等。狱卒们似乎钟爱铐子这一招,动不动就上铐子,最长记录用两副反铐,连续一百八十天!吃饭、大小便、月经都未曾松动过一点。
我们很难一一列举她究竟受过多少种虐待,据她亲口对张元勋所说。狱方将她投入到大号子中去,与社会渣滓们同居一室。每天晚上这些女流氓、娼妓们都要开会斗争她。这群泼妇根本不知道她犯了什么,只是拿些下流恶毒的瞎话骂她。她们骂她“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脸’!”于是这些婆娘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一齐动手上来厮打,群起而攻之。对于那些女犯来说,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争取“立功”的良机。对林昭的折磨越是凶狠残忍,就越算她们“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的“功”也就越大。林昭几乎天天在这群妇的撕、掐、踢、打中喘息。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这些泼妇甚至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狱卒们)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这群丧心病狂的妇人们身上,丝毫看不出女性应有的温柔,时代令她们人性扭曲,良知泯灭。手握权力的人处心积虑,想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尽量用到极限,而广大无权者对权势者惟命是从,千方百计迎合他们,生怕稍有抵触,便招来灾祸,为此,他们不惜出卖良知与人格,这就是中国的情形,不仅那个时代如此,今天仍旧如此。这个民族已经堕落。这些妇人的行径,无疑是在狱方的唆使之下进行,没有人撑腰,她们不敢肆意胡来。狱方甚至还给她们出点子,安排各种各样的花样。
狱方还指使狱卒试图强奸她,她被迫把衣服裤子缝了起来,衣服裤子缝在一起,方便时撕开,完事后旋又缝上。他们企图通过夺走她女性最珍贵的东西,来摧毁林昭的自尊心,自尊心被摧毁,斗志也就无存。不知道这种强奸的企图有没有得逞过,如果有,无论主使、教唆、执行者,都该遭雷劈、天火烧,世世代代永被诅咒!他们没有想到,这种禽兽般的手段,虽然会给人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却能成全一个女子的圣洁之名。二零零二年,巴基斯坦女子莫赫塔兰·马伊遭到四名男子轮奸,这四名男子在一个部族长老会的授权之下,光天化日之下,名正言顺地对一名柔弱女子犯下如此罪行。而他们的理由,居然是因为疑心莫赫塔兰·马伊的弟弟与该部族的一名女子有染,他们前来对此事进行报复,对莫赫塔兰·马伊施以轮奸之刑。在伊斯兰教世界里,一名女子,肉体与心灵遭受如此重创,她还如何活在世上?但勇敢莫赫塔兰·马伊没有就此忍气吞声,遮遮掩掩苦度残生,她四处上诉,对那些侮蔑、讥讽之词置之惘闻,甚至告到总统那里。当消息传开以后,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很多男士纷纷给她寄来信件,安慰她,鼓励她,其中有很多人表示,愿与她结为夫妻。后来,她致力与办学,倡导女性权力,成为巴基斯坦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莫赫塔兰·马伊遭受了一个穆斯林女性最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耻辱没有摧毁她,却使她变得更加圣洁。对于那些拥有金子般心灵的人来说,苦难和耻辱,是洗涤他们灵魂的药水。林昭何尝不是如此?
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使出多少毒计,甚至连最下三烂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他们给林昭喝下了毒的米汤,造成她腹泻、腹痛、虚脱,他们却在一旁偷着乐。
面对折磨,林昭除了继续写血书之外,另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绝食,一件是自杀。数不清她绝食了多少次,最长的一次是一九六五年,自三月六日交上血写绝食书后,至五月三十一日,历时八十天,天天写血书,狱方鼻饲流食。自杀有两次,一次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吞食药皂,一次于同年十一月十日用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两次皆未遂。自杀行为令人疑惑,这似乎与她“要将牢底坐穿”的誓言相矛盾,但是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两次自杀,都不至登即毙命。她是要犯,被“看护”得很紧,稍有动静,便会被察觉,更何况自杀。她应该已经意识到自杀基本不可能成功,所以才选择自杀。那也许对狱方是一个震慑,犯人自杀了,他们毕竟要负失职之责。如不成功,让他们手忙脚乱一场,借此表达自己绝不瓦全之信念,万一真的成功了,也好趁此离开这个黑暗的社会,免得徒受凌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