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52590
- 积分
- 17
- 威望
- 0
- 桐币
- 0
- 激情
- 45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9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2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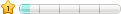
文都童生

- 积分
- 17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20-4-6 21:41:11
|
显示全部楼层
还乡记2
(四)
洋历7月初,各洋学堂在放暑假,我所寄住着的书山家近傍的这一个中学校园内,学生们在梅雨季的雨水声中考完了期终的大考,都陆续回了家,教职员工无特别工作要在暑假中加班的,几乎都不见了踪影。
我那个姨父不愿回家,草台班请他去操琴和做台务的指导,我更见不到他。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到了旧历七月半的中元节,这一天是洋历8月18,乡下唤做鬼节,大小寺庙里称这天为盂兰盆节。依习俗,家家免不了要忙着放河灯、祭祖、祀亡魂、焚纸锭。节气上已过了立秋。“立秋分早晚”,白日里太阳虽则猛烈,秋老虎淫威正盛,早晚可有了一丝凉意了,就在这一天的夜里,远远的有人在野祭之后燃放炮仗的啪啪声和暗泣声飘送到了耳畔,我听了不禁心生悲凉。
日间我收到法专来信,被告知受时局动荡和办学经费积欠原因所致,学校不能如期开学,开课日期另行通知。
时间又过去了多日,在这中间,我于学业上一日也没敢放松过。几册英文课本与一册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厚书我能倒背如流,就是那一册平日不大爱看的几何学书后,让人开动脑筋绕来绕去才能解答出的练习题也难不倒我。
暑假已结束,天城中学校内学生们开课了半个月。
中秋节前一日,系洋历9月15,天气非常好,朝霞已在东方微露,澄碧青空中飘浮着几缕棉絮样白云,这天是学生们照常在上课的礼拜四。一大早我就起床,穿好衣服鞋袜,叠好被子,漱洗后,带上干粮和一套换洗衣服,就步出书山家,步行六十多华里旱程赶往县城家中去与家人团聚。我知道日间行走在路上,太阳暴烈,临出门我还不忘了找了一顶帽子来,就这么端正地一扣扣在头上。
傍晚时分我迈进家门,同爸妈打过招呼,洗了个热水澡吃了晚饭就早早安歇了。第二天即是中秋节,爸妈一大早就特意准备好早饭等我起来吃。
我昨天白日里赶了一整天路,昨晚上沉沉睡去,第二天的中秋节的侵早,我一觉醒来后感到浑身酸痛,尤其一双脚痛得厉害。 座钟敲打过八下,时间已是上午的八点钟,我才起床漱洗后,一瘸一拐的走上厅上来吃早饭。
因为我上次离家还是在旧历正月的初七日,距此次归家已逾七个月了。爸妈这时早饭早吃过了,他们留在那里只是要当面向我询问我这在外面七个月来的情形,问我康复得怎样,学业怎样和几时开学,钱够不够。等我一一回答他们后,我爸爸就板起脸来训斥我一句“在外面要早睡早起,不能够像今天在家里睡到八点!”紧跟着,不知怎的,我妈妈又向我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来数落我。我想辩解,可无从开口!
“爱屋及乌”这一句话我如今倒真可以反着来证实它。
接近正午时候,家中陆续来了一大帮亲戚,是爸妈请他们来家中作客的。乱糟糟人客挤满厅上,多在说着一口糯米饺儿似的江淮官话,他们多半是这一个桐城县城内外的目不识丁的粗人。相互间说着一些套话空话,大声谑笑,随意地吃着瓜子,抛吐着瓜子壳,将大口痰吐在地上,然后用脚那么随意地一踏。
他们交谈中有人说到黄甲铺,就有人“山猴子!山猴子!”的大叫起来,说及双港铺,也就有人面露不屑说“那是乡下!”。也有人在问我我在念书的安庆城,究竟有没有这个桐城县城大?长江是否也同我们这个门前的龙眠河一般在天旱时会干涸?我真被他们问得哭笑不得。
我原不想坐到酒席上去,被他们拖拽不过坐了上去。我外祖母也在这席上。我第一个就向我那外祖母敬了一杯酒,说了声“外祖母中秋节好!”没成想这激怒了我妈妈,她就用了她那一口地道的这桐城县城的当地的江淮官话的方言土语,毫不客气的当着大家面前指责我大不孝顺。原来我妈妈平时在家里早立下规矩,我们小孩子见了外祖母不可叫外祖母,一定要称呼祖母,叫外祖母是万万不可的。接着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我盛了一碗米饭在吃时,我又淘了一大碗汤在喝,我妈妈就又丝毫不顾情面的在酒席桌子上大骂我糊涂,原因是她有一个迷信,就是她平常已告诫过我们,吃饭时不可淘汤,淘汤出门下雨。
紧接着,我那大姨妈家大表姐又用了一口同我妈妈绝没两样标准正宗当地口音江淮官话对我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他们的话一定要听!”
我被窘得满脸通红,草草地扒了一口饭菜就借故匆匆地逃也似的一个人先跑下了酒席桌子。
我一个人找了一处没有人客的地方,独自枯坐在那里发了一小会呆。
啊啊!爸妈生养了我们兄弟三个,大哥和小弟于外省念大学,一年中也难得回家一次,一家星散聚少离多。我虽则出门读书离家最近,可这次也是时隔七个多月后第一次归家。此刻,我脑中思绪同纸片样纷飞,我眼角脸上不觉又滚落下了两行冷泪。尤其令我无法接受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爸妈与我本应互为最亲的人,不知道他们可为什么要这样好似有绝大冤仇的待我?!我在家中,既然这样的被爸妈怒对斥责,我又能怎样?!啊啊!我能做的只是沉默,心内想的只是赶快的逃离。
至此 ,我不能不逃离这个伤心之地,对这么一种软语柔声的方言土语,我也不能不心生嫌恶!
“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天城校园内那一排笔立的喜树,宽大叶片子也开始在秋光中一日一日的变黄,一簇一簇的果实缀满枝头,如同一盏一盏喜气高悬的小灯笼。有一阵秋风拂过,叶片与果实也有的纷披掉落到树下的泥地上,却也烘托出一片恬淡圆融的氛围。
我又回到了双港铺已有三天了,这次中秋节的返家,除却从家中带来一包供我读书生活之用的银元外,同时也带回了比从前更加重的绝望、伤心与失落。
“过了重阳没有节,不是雨来就是雪。”中秋节又已过去了一个月光景,天陡然似掉进了冰窟窿。白日里农人们打赤脚在水田中猫着腰挥刀收割稻谷,稻谷高过人胸。书山家阶前,被我们唤作夜饭花的紫茉莉开了,饿饿的花香阵阵熏拂,醉人如酒。
时光又一日一日地过去。
不知不觉中,入秋后我的肝炎肾炎的病症竟然也奇迹般可喜的得到了痊愈。我的面庞不再发黄浮肿,睡眠好起来,饭量也大增,体力精力亦一日比一日愈加充沛旺盛,心情自然又变得活泼开朗乐观起来。我于洋历11月初头一个天气晴好的周一早上乘船去安庆城内的那个同仁医院里做了一次复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我这一次进安庆城不单只是在同仁医院内做了病后的检查,顺便我又跑回法专校园里探看了一次。眼前的法专已经同我半年多前离开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整个校园几乎没有人迹,冷冷清清没一丝一毫在准备重新开课的迹象。就是在我们之前的住宿舍前,因为长久没有人居住,也长满了杂草。我想于校园中寻找出一个我认识的师长熟人来打听一下关于我们何时可以重新开课的最新消息,也终于办不到。
高天里的雁阵把芦花叫白的时候,我也曾独自一个人跑到双港铺近傍南北湖沼里去看芦花。
记得新近有一个诗人在说:
“这秋月是纷飞的碎玉,
芦田是神仙的别殿”
皓月芦花,眼对着这一个清景,不觉间我又滚出了两行清泪。
(五)
我自从搬住到凌家墩,绝少再上到天城校园内玩耍倘徉。有时候有事情要办,非得去一趟双港铺街上不可,我必迈开脚步子径直地从南往北地贯穿这个中学校园,在校中打一个过身,回来的时候必又反着方向地依着原路地走回来,在这中间,倘若碰见熟人,我只冲那人点一点头,远远地抛一个笑脸,脚步子匆匆地却也不作片刻停留。
双港铺街南面的乡下人,但凡往来街上,必从一条贯穿这个中学校的看起来并不见得怎么宽阔的土路上过身,不独是我如此。
乡间风景质朴而清纯,真无处不在。就是行走在这么一条土路上,我眼前同样呈现令我心生欢喜的无限风情。
一户人家养了头配种的公猪。公猪在主人的引领下,扭动着屁股晃悠着行进在配种途中。鹭鸟飞起飞落,片片水田望不到边际,秧苗叶片子上擎着晶莹的露水珠在发着碧油油光。春光老去时节,野蔷薇丛丛开放,油坊飘出香气直往人的鼻孔里钻。炎天烈日里,土埠头,濠水边,枫杨树上知了声此起彼伏,白条鱼贴着水面穿梭地游,有人走来,唰地发一声响,在水中散开不见了,溅起白水花。
土路上行人皆徽赣移民后裔,在说来自江南的赣语,发声脆而硬。
我蛰住书山家,也许是一个人在房内复习功课憋闷得太久,一天,我忽然起了带上纸笔,上到那一幢古老的藏书楼上去抄录古碑,放松调剂自己一下的念头。
天城中学校内一个老年的杂役,矮小的身材,耳朵有一点背,口齿也不清,大家叫他聋子。认得我,把我让进了楼。
“桐之西,前天柱,后兔子,左大龙,右栲栳,中则半平岗、半平原,经双港突起大阜,顶平如掌,围高如墙。前人建寺其上,名梵天寺,又名梵天城,寺言其舍,城言其基也。”
这个楼原是中学校前身,满清时于此处所办书院遗留下的一百五十余间房舍中的一部分。楼内有古碑多通, 聋子一一指点给我看。眼前的两方,一方是《梵天寺长明灯记碑》,另一方是《保田庄屋记碑》。我用眼光匆匆掠了一下,另外一角里有一方古碑,是《天城书院条约碑》。一通满清道光时古碑前,我立住了,撰写者为彼时里中名士刘存庄,碑名为《梵天城记碑》,我几乎伏下了整个身子去抄写下了这一节文字。
时间进入中华民国十年,即洋历1921年末,天气异常寒冷。我的手冻得僵硬不听使唤,搁下纸笔,我将两只手插进棉袍子内取暖。聋子见状拖我过去喝茶。
推开门,我一脚跨了进去。 隔壁房里,两个人在烤火,燃着的炭火盆上正吊烧一只注满水的铜茶壶,茶壶里水烧沸了,在发很大声响的滋滋声。见我进来,他们立起了请我来坐,聋子将铜茶壶自熊熊炭火上取下,又拧开了一个洋铁的小茶叶罐罐,抓了一撮本地产大叶子茶到一只杯内,沏了茶给我。手舞足蹈的,口中说:“好!”一面用一只手在我背上用力地一拍。我被他那么地一拍,手中的茶水全洒到了棉袍子上。
烤火的两人,我认得他们,是这个中学校的教员。身材高大的是钟子勉,另一个叫桂立中。钟先生我本来就是很熟的。他们在说着流传于潜山县和桐城县这个西乡的一个荒诞传奇,名叫《狐坟》,讲明朝潜山县书生徐桂和一只狐狸的事。我围坐在炭火旁,烘烤被茶水洒湿了的棉袍子,一面也就听起来。
听了一会,我又在炭火的盆旁立起了,拿一只烧火钳不住的在拨弄着炭火,让它燃得更旺些,我索性又把我湿了的棉袍子从身上脱下,放到炭火上去烤。又过了一息,这时候,我的棉袍子差不多已经在炭火上烘烤得干透了。
钟先生是香铺人,讲江淮官话,声如洪钟,掷地有声。桂先生是本县青草塥人,一口纯正西乡赣语,自然又要多一份儒雅的气息。他们讲了许多,可我只记住了四句:
“细雨洒芭蕉,
孤灯独自熬。
不嫌奴貌丑,
陪君度良宵。”
聋子用铜茶壶往我们茶杯中加注烧开的沸水。一面自说自话着,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明天就是大家口中在说着的洋历的新年了,即中华民国十一年1月1日。 校园里,学生们来来去去地走动着,一个一个脸上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似乎与这个校园早融为一体,沉浸在一种希冀喜悦憧憬中。他们要召开一个盛大的庆祝大会,就在今晚这个中学校礼堂内,庆祝洋历1922年的光降!
晚上,我在书山家默默吃过夜饭,早早睡了。
朝日的一支支绯红箭射上了窗棂,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的侵早。旁边的这一个中学校正式放了年假,小小双港铺街上,人声鼎沸,有人在放炮仗,种种迹象都在宣告,这日是洋历1922年的新年。
新年新气象,我一大早就起来,听到院子中有很大声的鸟叫,抬头一望,两只花喜鹊在隆冬时脱尽叶片子的榉树上叽叽喳喳地闹着。“莫非有喜事么?”同样早起的四奶奶,见了也这么地在说着的。
我打算上一趟街上,去探听一下法专的消息。走到凌家墩小村落北首,远远地望到设在华大商号内的邮政代办点里那一个小邮差,正自天城校园里一路跑下来。过濠上石桥时,也望见我了,就高举起一封信在招呼我。
我三脚两步跑了过去,自他手中把信取了拆开一看,我更加高兴得要飞跳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太好!”我接连大叫了三声太好了。原来这是法专寄给我的一封快信,信上说法专已经于1921年年末正式复课了,特此通知我火速到校报到上课不得迟误。
小邮差看我疯癫样子,愣住了,之后也就高笑起来在替我高兴。
黄昏时,南面濠水石桥上又出现了三个身影。前头一个是书山,最末一个是汪玲燕,走在中间的竟然是文绣。我惊诧得张大口子说不出话。我把他们三个迎进四奶奶家,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三个一个劲的笑而不答。“文绣不是好好的么,哼!汪玲燕乱说文绣死了,害我上次白白伤心了一回!”我在心里暗想着。
这天的晚餐由我做东,自街上买回了酒菜,酒席就摆在四奶奶家高大气派的厅堂上,他们知道我即将动身往省城里去读书,继续已中断的学业,一齐举杯向我庆贺,我也回敬他们,尤其是见到文绣,恍若隔世,我更是喜极而泣。吃过了鱼,也吃过了肉,酒不住地往喉下送,个个的脸色红润了。喝了两满坛白酒,又喝了元红,酒我们怎么喝都是不醉的。我们四个的说笑把四奶奶家这个厅堂都要给震动得发起抖来。
“当当,当当……”四奶奶房内起了那只马球牌座钟的敲钟声。被钟声惊醒,我眼前一片黑暗,原来我只是做了一个梦。租住在这院内另两间房里的学生们,大约是刚参加完了夜里中学校的庆祝大会,兴奋得很,只听见这几个学弟学妹还在各自房内隐隐的说着话的。
“细雨洒芭蕉,
孤灯独自熬。
不嫌奴貌丑,
陪君度良宵。”
无心的, 我的口竟念出这四句……
(六)
湛蓝湛蓝的冬空,真蓝到人的心里去了;冬空之下:大沙河,挂车河两条碧流呵抱着的这么一列窄窄土岗之上人烟聚集。岗下湖沼片片接至天边。
“西北环山,民厚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而文,历出闻人。”
潜、怀、桐三县交汇处原是泽国水乡,数不清的河流水系密如蛛网,自西向东串起珍珠颗颗,源潭铺、青草塥、新安渡、金拱、凉亭、双港铺、练潭、罗家岭,居民多徽赣移民后裔,吃一泽水,习俗一个模样,土白说南方方言赣语,不尽是一县更像是一县。与这北面说归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的桐城绝大部分地儿大不同,这其中的青草塥、新安渡、双港铺、练潭、就是桐城旧时西乡地界。春夏涨水,潜、太、岳、霍、英、怀、桐各县砍伐的原木与毛竹扎成排筏顺流而下,门板般鳡丝子追赶鱼群从长江上溯而来。河流两岸满眼皆肥沃而极易耕作的湖田。
这洋学堂两字校名源自校址古名梵天城,不在平地,矗立地面上十数丈高,“四围环以土城,城外环以水濠,自然天成,风景绝佳” 脚畔一列东西向小小石板街铺只缘地理上是“南北川泽,左右陂湖”南北皆可行船,因名双港。
立在小小石板街头,抬头南顾,高耸着的便是那一个土人呼作洋学堂的中学校的校园,土人或传为商纣王登基之所。西北角上,高约数丈一漏斗型高台,中有一洞,深不可测,土人唤作妲己台。有苏姓人家居住于此。迁自江南的谢姓人家建筑的祠堂,雕梁画栋美轮美奂。大沙河河汊与岗上街铺相接。古书上呼为挂车巨溪的挂车大河紧贴石板街北侧土岗日夜奔腾,发源于大别山余脉,由山中泉水汇集而下,途径挂车河镇、老梅树街、新安渡口、双港铺,最终汇入菜子大湖。
两条大河水皆清澈见底,产野生鲶鱼、鲤鱼、鲫鱼、甲鱼、白条、鳑鲏、黄鳝、花鲢、白鲢、黄骨丁、鳊鱼、翘嘴鲌、草鱼、青鱼。两岸各类野生植物生长极为繁盛。有兰花、竹林、桃树、桑树、枫树、杨柳,近岸水中生长莲藕、茭白、菱角、芡实、芦苇和各种香草。大量禽鸟栖息其间,如鹭鸶、翠鸟、野鸡、黄鹂、水鸡、野鸭、大雁、鸳鸯、鸬鹚。河中产黄沙、铁砂。沿岸低丘多黄麂、山兔、碗口粗大蛇。临水矮埠生长一种野生白蒿,书上亦称篓蒿。春日里当地居民采摘制作最具本邑特色蒿子粑粑。制作时主要食材有白蒿、米粉(本地做蒿子粑粑几乎不加糯米粉)、腊肉。制作食用这种粑粑以农历三月初三日为盛。乃徽赣移民带来风习。
依傍街铺,青、白、麻褐色条石垒就埠头,泊靠江船,运进省城安庆转口至此咸盐、洋油、洋布、杂货,运出稻米、湖鱼、桐油、生茧。早晚,成群妇人来此淘米洗菜洗衣浆衫,棒槌声、捣衣声、说笑声络绎不绝,连成一片,此起彼伏。因临大河,街中并无水井,有体格壮实劳力来此担水灌满灶间陶瓮瓦缸。有好事者,担来老糠,倾倒妲己台顶洞内,必自距此东去数里开外河中浮出。
自木闸乘船穿菜子湖至长江南北各大小码头极易。有人也欢喜自高岭山搭贩运稻米帆船出门。若与船主人相识,搭船分文不取。油桐花开的春日搭船,你只须出一点小钱,船老板必欢天喜地一反平日极节俭饮食,在船中请你吃湖鱼、吃腊货、吃不花钱的时新菜蔬,必要你喝稗子酒,给你泡桐城大叶子茶。前清阮先生(阮强,字仲勉,桐城人,清末民初教育家。)于此倡办公立天城两等学堂,是拾陆年前事。
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洋历元旦,我一早起床刷洗后,在房里攻读英文。我接大哥来信,他要我报考沪上一所大学,我不能不下一些功夫。
四奶奶和孙女小翠在灶间烧火准备着早饭,四合院落内较平日清静不少,租住的学生各自回了家,平常时节在院中踱着方步子的几只大麻鸭不见了,体肥毛亮的黑毛猪伙着几只笋壳鸡在院门外麦垛旁觅食,还时不时的哼哼唧唧的。
我在房中手翻书册,翻看了一忽,心思很乱,一颗心怎么也不能平复宁静下来,终于把书本子就只那么地一丢,早饭也不吃匆匆跑出四奶奶家,上街上去打听消息。
华大店内,朝日已铺上大香樟木头柜台的面上。一个大脸妇人正在柜台前购买红糖和洋油,看见我跑进店来,朝我憨笑了一脸。柜台后面立着一个人,正是这一个石板街上最大商号的主人。这人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盘得一手好账,身兼本地商会会长。因为同我那个平日里最欢喜与人结交,朋友满条街的姨父认识,我每次上街上来,他一见到,就笑笑的学着我那个姨夫有时称呼我的口吻,称呼我为姨侄子。
此时见到我,他照例笑笑的喊我:“姨侄子。”
我也同他打过招呼,翻开一堆报纸来看,一面向伙计打听消息。法专消息照例无从打听。日头的光柱子从玻璃亮瓦上直射下来,跌落到方砖地上。店里的人出出进进的,各人都各自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店堂内“宝”字牌座钟,时针和分针构成一个大大的九十度直角。我在听过耳畔响起当当当当的9句钟的响铃后,喝过伙计泡的一壶热茶,坐等了一忽,才又跑出店来。我想去河埠头运邮件的木壳船上,试看一看能否等到今天新邮送来的报纸。
天气出奇的好。这一列土岗上的田园、村落、人家、房舍、市集躺在湛蓝的天幕下懒洋洋的沐浴着冬日。
石板街上赶早集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有卖鱼卖肉卖菜的,有卖稻谷卖米卖糠的,有卖牛卖猪卖鸡卖鸭卖鹅的,有卖柴草、木炭、篾器的,这些是席地和露天交易。两旁店家,拆了排门招揽生意,有人跑进跑出,买黄烟卷烟,土、洋布匹,买油盐酱醋茶酒,买窑货瓷器,买粥、草鞋板子(亦作朝笏)卷油条、水饺(实为馄饨)包子馒头,三个铜板管饱,茶馆子饭铺子当街挑出布招牌,伙计手提铜茶壶,当街吆喝:“东濠水泡桐城大叶子茶,好喝不贵!”街上有杂货铺子、膏药铺子、牙医铺子、剃头铺子、成衣铺子、花圈铺子、木匠铺子、铁匠铺子、窑货铺子、杆秤铺子、客栈、银行、邮政代办点。
人家青瓦屋顶,炊烟袅袅,朝日射人头上、身上,射石板街面上,浮泛淡淡青辉。收捐课税人穿插其间,我知道平常时节,这人与木崖乡公所乡长、保长(此地为双港铺保)、师爷、乡丁,寄驻中学校一个院内,不在这街中。
洋历元旦日各学校必照例放假,早上自中学校过身,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的,在水塘边一株老树下,我见到一个金姓小学弟手拿一册洋书在高声念洋文。他见我,同我打过招呼,又开始念他的洋文了。
石板街南北两侧河埠头,泊着比平日里明显要多许多的木壳帆船,装来整船瓷器窑货,在等来人搬运上岸。米粮老板忙着将稻谷装船,载往下江贩卖。远处湖沼里有人在收割变枯黄的芦苇 ,地里的豆、麦已经长出嫩苗。要不了多久,这些东西就会长得很大,在春日里开出有撩人的花香的花。
我在石板街中逗留了整整一个白日,当从南向的一条子街步出时,暮色已从周遭围拢起来。人家放养在野地里的猪鸡和别的小畜牲也回了圈舍。在走过铁匠门前,一只大狗在暮色里汪汪的叫。
凌家墩四奶奶家厅堂上燃着灯火,我吃过夜饭默默进到租住的房里。黑暗中摸索着了一盒洋火,取出一支,点亮了房中的那一盏美孚洋油台灯,坐在灯前我发了好一会呆。在这么一个隆冬时节偏居一隅的乡下的小村落里,夜深了,寒气沉沉,桌上一方砚台,结了冰,我用口呵气化开,拿一支毛笔,蘸了墨,想在簿子上记下一点什么。
我又想起了早上碰见的那个小学弟。
春间因病我自法专休学,寄住到中学校那个木楼上。一天听到人声嘈杂,见楼下有个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被人围着。问急急忙忙气喘吁吁跑上楼来的森来,答说是乞丐,奄奄一息了,大家正着急不知如何是好。我往楼下跑时,一个少年已一手推开众人,将一件棉袍脱下覆在那人身上,也不说什么,背起那人奔北面街上去了,旁边两个貌似是他同学一路跟去。之后大家也就散了。两天后森来忽然面露喜色的告我,那个少年救了那个人一命。少年姓金,是这校中学生。
楼下一株满树繁花的棠梨树下,一个少年领着三个衣着非常考究的小女孩子在玩耍。见我,朝我笑了一脸,说姓金,那天救人的是他。我才用心打量他:人长得很文弱,谈吐儒雅,同那天好像换了一个人儿似的,完全看不出那天的勇猛强势。相貌上异于常人,一头黑发,发式为城里必才见到乡间倒难得一见顶顶新潮的一个漂亮中分,梳洗打理得那么整齐光亮。我心里琢磨,他这必是抹过上好头油和打过上好发蜡的。缺了一只右耳,嘴巴生得很不周正,向一旁歪斜。 他爽快地自报家门:家在三十华里外张云乡青桥保。父亲名荫程,字来程,号振侯。早年留学日本,供职皖省测绘局。全家现在搬住省城安庆倒扒狮街。本人名丽生,字兆松,号镜清。光绪丙午(公元1906年)又四月生人。三个小女孩儿是他三个妹子,分别叫桂生、兰生、菊生。
之后我常常撞见他,人喊“没耳朵”或“歪嘴”,他必要发怒。他有时候忘记了也好好的答应。
知道我住校中,他偶尔也会噔噔噔的踩着那个木楼梯子上到我房间来玩。我才晓得,桐城的西乡有四位显赫绅士,名号中都带个“侯”字,人称“四侯”。他的令尊名列其中,是四人中最年轻彪悍富足的一个。这个洋学堂开办当初,捐出过一石种(约合10亩)租田,聘为名誉董事。经办这个事情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这个洋学堂中做会计的我那个姨父。
可是此时我不会想到,数年后这个小学弟自这儿毕业,念了大学,又回到这校来教书,又过了几年做了这校的校长,忽然一天就死在这校里,年仅三十二岁。他在西乡名气很大,妇孺皆知。关于他的死因:有人说是被人一枪毙命,有人说是吞金而死,有人说是暴病而亡,至今成迷。死后多年,还有人谈论他,有人说他是负隅一方的土顽,有人说他是保一方安宁的绅士,有人说他是令人尊敬的这堂堂的洋学堂的一校之长。我更不会想到,又隔数年,另一个我认识的小学弟,大学毕业后同样回到这校教书,同样做了这校的校长,人生巅峰时候身兼数职,几百条人枪,在这个桐城县一县之中,人都视他为“王中王”,他同样英年早逝,令人痛惜!你若一翻本地县志,在关涉这个县的许多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的记载中都不难发现他的大名。他是桐城县西乡青草塥小河沿人,这人姓张名护棠!
(七)
双港铺小小石板街弯弯曲曲成个大大的英文字母的“S”,长不足一华里,两侧房屋接瓦连椽一派徽风。行走街中抬头上望,人家屋瓦之上触目满眼皆是高高马头墙。有的人家马头墙重重相叠,多可达五重,有人给取了一个文雅称呼“五岳朝山”。
侵早落了一阵子冬雨。东北方向鸭子湖里,菜子湖里于前一晚以排枪火铳猎获的大雁、野鸭,还有古书上称为鹄的天鹅,肥都都的,有人用细棕麻绳缚定,十二只一打。步行个六七华里、十几华里担来街中售卖。石板街的上街头外,那有三进房屋两个大院落徽式气派的谢家祠堂前场坪上,较平日里冷清不少,只有一两个人立在那里,东南方的苏姓人家门前白石牌坊下赶早集人,三五成群结伴而来,一路说笑着,络绎不绝。白石牌坊傍一棵大皂角树,在冬日里脱尽了黄叶,光秃枝丫直刺天空。
我挤身在熙熙闹市中,在两耳充斥嘈杂市声中跨进华大商号店内。内设邮政代办点的那个认识我的小邮差见我到来,知道我心思,笑盈盈地迎上前递给我一封信件。上面赫然注着寄自沪上,我认得那挺拔秀逸墨迹,正是我大哥的手迹。我顺手讨要过一把小刀将信封裁开,掏出信展开来读。同他上一次给我的信并无不同,我大哥他那意思仍是劝说我应该早早另做打算,重新报考沪上一所大学,不要做个白白坐等消息下去的呆人。待得明年春暖花开日与他聚首那个春申江畔十里洋场。因为是深知我的人中的一个,知道我生性纯良,但是也不免有时有痴拙毛病,末了他仍然不忘了引用我爸爸常常在训诫我们兄弟的话鼓励我:“生如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当有不屈之心。”
他说的没错儿,看来我真的不得不重新要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从头再在这个方面来下一番苦功夫!农历春节,我打算不回桐城县城的家中了,独自一个人埋头在这个旧时西乡乡间用功苦读!我在心内暗自打算暗下决心。
白昼短暂到只允许乡下农妇们做三顿饭的工夫。
时间又已经到了洋历年头旧历年尾,天气接连落了一礼拜冬雨,异常寒冷,滴水滴冻。天色阴沉沉的。
“天必落雪才会放晴。”我往日单薄经验告诉我。
石板街上店铺点起了灯火,白花花的洋油灯光透过擦得清亮的玻璃灯罩子把店堂内照得雪亮。也许是天气太过寒冷了吧,伙计们英雄所见略同,搬出大铸铁炭盆,支起新栗炭烤火,那些燃着的新栗炭在炭火盆内吐着金碧火舌,哔剥爆裂着快乐火星。
恒泰、德友、善交等几家章姓人家开的茶饭铺子及中药铺子李同春号、方春霖号、下街头寿乐堂里,以及何姓人家开的何泰裕号南北杂货铺子都有很多乡下人聚拢在那里出出进进。
逢旧历三、六、九,这一条充斥烟火气小小石板街铺必照例成为牛羊猪鸡等牲畜和乡下所产土棉纱极重要交易集散地。影响所及北至金神墩,南至黄马河,东到罗家岭,西达青草塥的旧时桐城县西乡的大部和南乡的一部,以及邻县的怀宁县的北部和潜山县的东部,方圆百数十华里地方,或远或近,或大或小,或丘陵山岗,或河湖圩区中不可数计村落人口烟火万户人家。
在这个旧历春节的前后约摸一个月光景,小小石板街上买进卖出商业照例进入鼎盛时候。
所售卖商品当中除出那些应节老品种人家迎神祭祖必备的香烛裱纸,烟花爆竹,对子年画,南北杂货,糖食糕点及送人或自用年节必备品外,自然也缺少不得从上下江泊来的洋油洋灯,洋火洋烟卷,洋纱洋布,洋伞洋碱,洋钉洋铁,洋药洋纸,洋笔洋墨水,洋蜡烛洋年画等新奇古怪高端新潮紧俏货。此外还有乡下人绝少见过的进口饼干,海带鱿鱼干之类海味。
华大字号一次购进十几、二十几条船的美孚洋油,那些洋油分装在一个一个草绿色方方正正洋铁皮子罐内。洋油被伙计们肩扛手提自码头搬运进仓库伺机而售,他们出出进进的忙得不亦乐乎,大汗淋漓,兴奋并快乐着。天气太过严寒,我两只满是泥泞的脚冻得像被马啃过麻木疼痛。在一张榉木大椅上坐定,烤着火我抄起一册积着厚厚灰尘《地理诀要雪心赋》的风水书心不在焉翻着,一面用并不纯粹地道西乡赣语同他们大开起玩笑,惹得那些伙计哈哈大笑。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空果然洋洋洒洒的飘落起了大雪花,不一忽,对街人家屋顶和石板街上就被覆了厚厚白雪。有人脚穿带钉齿牛皮雨鞋手撑黄油纸伞,有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大风大雪中穿梭。漫天大雪无声落着,有一种虚无缥缈梦幻感觉,不像是真实的存在。
我下定了心思报考沪上的一所大学,需要购买备考书籍,委托这店内邮差为我代办,下过定金,脚踏一双圆口布鞋子深一脚浅一脚跑离街中。
旧历新年脚步迫近,旧历新年气息越发浓烈,长年出门在外的人都陆续归家,准备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欢天喜地过农历的新年。
长久不回家,我爸爸推开县政府冗务,跑了六十华里旱程,亲自从桐城县的县城来到双港铺,特意为了来看我。同时给我带来我需要开销的金钱。平常时候在家中,我爸爸训斥我最多,我知道那是他对我最为担心,老要对我放心不下。我们兄弟三个,他放在我身上心思最重。
时间一长,我遂养成个习惯,我遇事通常不与他商量让他知道。因此在家中,我爸爸常常大发脾气大骂我,像个暴君,将我当作臣民,践踏蹂躏。但我不记恨他。
父子见面,可说的极少。他明白我的希冀,他明白我满打满算今年才只就十八岁。他更明白我离家独自一个蛰居这个西乡一隅,正拼尽着全部气力,追逐梦中那一座七宝楼台!
返程前,我爸爸同我,还有我那个姨父在石板街上恒泰茶饭铺子吃了顿饭。我们要了鱼圆子、肉圆子、猪腰花、猪肚四个水碗,外加两个干碟,三碗米饭。掌柜的是一个叫章毛氏的老太太。饭菜非常可口。待到大家放碗时,我爸爸始终不怎么说话,更少动筷子。步出饭铺子,大太阳底下,我看到他两眼湿莹莹的。
清代里中名士刘存庄称:“桐之西,前天柱,后兔子,左大龙,右栲栳,中则半平岗、半平原,经双港突起大阜,顶平如掌,围高如墙。前人建寺其上,名梵天寺,又名梵天城,寺言其舍,城言其基也。”今人亦有:“四围环以土城,城外环以水濠,自然天成,风景绝佳”之誉。
地当冲要。由于历史的瓜葛和现实的考量 ,天城洋学堂校内,除出几百名学生和几十位教职员工,同时驻有木崖乡公所和乡保联防大队计百十条人枪,另外有两户人家。西头一户人家姓王,东头的一户姓汪。汪姓人家有十二间大瓦房,租种校中一石种租田,每年秋收时,洋学堂里就照例派人过来象征性的收过几十斤糙米权作一年田租。这工作,通常由我那个在洋学堂里做会计的姨父,受了校方的指派,上到各租户家里来完租。校外东濠冲里,汪家尚有块自己保有的三石种水田,约摸20来亩,长年雇用了三五个长工。这家男主人的户主死得早,当家的是一个叫汪潘氏的老太太,有三个儿子,次子未成年就夭折了,只剩有叫德祥的已娶妻生子的大儿子同排行老三的一个还是小孩子的小儿子。
早在数月前的旧历六、七月,赶在立秋节气前,乡下人就在种有稻子的水田缝隙播下泥豆种子。待到当年新稻米如金如玉,颗粒归仓。泥豆成熟。小孩们帮同大人们一棵一棵自田中拔起,收拢来打成捆担回家去。收获泥豆,照老习惯,搁到腊月里打豆腐吃。旧历新年里吃的菜品中,不论水豆腐,豆干,豆腐乳都离不了这豆腐。乡下人家一年四季中都有人在家中酿糯米酒吃,自家酿酒自家吃。街上酒坊也有售卖。十冬腊月,专门酿酒师傅肩挑背负酿酒器具上人家门庭酿酒的更不稀奇。酿个糯米酒,磨个糯米粉,打个糯米糍粑,炸个糯米圆子、烘个糯米粑粑,遇初一,十五,人家里大人小孩子要煮个汤圆、元宵吃,均少不得本地出产上好雪花糯。
冬闲不闲。刚跨进旧历腊月门槛,四奶奶家里就忙得不可开交,整天人客进出,乱哄哄的,实在不成个样子。先是四奶奶将纺纱织布积攒了一年的老土布,组织家里人投到用枫杨树皮熬出浓汁的大锅里蒸煮上色,待老土布由原先的白色染成灰蓝,根据家中各人所需,拿去街上请师傅缝制成新衣新袜子。接着是杀年猪打塘鱼,杀鸡宰鹅腌制腊货。腊月腊八腊八节,熬腊八粥,磨糯米粉,打豆腐,酿糯米酒。
初九老太太70大寿。“男做九,女做十”,本地风习,不能免。这一户虽说是个外来户,在本地原没根基,一切靠白手起家。但经过这多年吃苦持家得法,今非昔比,虽称不得豪富之家,但却也是在中产以上,这凌家墩小村落门面户。
多子多福,瓜瓞绵绵。老太太生养无数,长成的有二儿七女。两个儿子在本乡和外乡当乡保长,女儿们出嫁这附近七村八落。这样一来,整日迎来送往客人自然又不能少。乡下人大嗓门,礼数多。来客必要吃饭,吃饭必要吃酒,吃酒必有人吃醉,吃醉必要留宿。我租住的房间由于是木板墙壁,隔音不好,有好几晚留宿客人鼾声如雷,弄得我整晚都不能入睡,大白天哈欠连天,更无心读书备考。
这终归不是个办法,我同我那个姨父一商量,决定仍搬回洋学堂居住,为了方便,就近在校内汪姓人家搭伙吃饭。这事一切办得特别顺利。
除夕那天大清早,我从街上购买了两起红纸包封细点心给两家拜个早年。四奶奶特意追出院门要我这晚上在她家吃年夜饭守岁。我因为已搬住到洋学堂,下到四奶奶家要过土城墙,过一个高耸土坡,过护城河。便用了一个“隔山隔水,大有不便。”的玩笑话谢绝好意。
在德祥家吃年夜饭大约是在这晚戌时的八点。在被菜油灯盏照得灯火通明的厅堂上,身着过年时才穿着上身的新衣服,大家围坐在酒席桌前。欢乐融融。这晚年夜饭非常丰盛,开席时大家先共同喝过一通糯米酒,接着德祥的妈用毛竹筷子夹住两只炆蛋搁我碗内要我吃,老太太高声说:“这个是大元宝!二哥哥吃了新年发大财!”她三岁大孙子庭杰听过这话,忽然眨眨眼睛,一脸疑惑:“咦,元宝怎么像鸡蛋咧!”大家哈哈大笑。德祥的妈,那一个油头小脚老太太笑出了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