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0384
- 积分
- 73
- 威望
- 548
- 桐币
- 0
- 激情
- 5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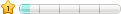
文都童生

- 积分
- 73
 鲜花( 0)  鸡蛋( 0)
|
 发表于 2004-10-6 22: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04-10-6 22: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一段时间跑上图特别勤快,总是不停地借书还书。前些日子为了准备桐城之行,专门借来了一本桐城派的书籍来研究,《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这是桐城派研究会出版的一本专著,内有桐城派的概述、传记和名文。一册在手,很是实用。读下来才知道,桐城中学由吴汝纶一手创办。百年校园里到现在还有姚鼐手植的银杏树和左忠毅公的祠堂。当初中学时候熟读《左忠毅公逸事》,大学时候听讲《狱中杂记》的情形一下子历历在目起来。都是桐城派的文章。都出自这个看似寻常的县城。桐城是清代文学重镇,在安徽。我总是想着要去趟安徽,准确地说是桐城和天柱山。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是桐城人,曾经上课的时候用桐城方言腔调读过方苞姚鼐的文章。老师说,“天下文章,归于桐城”,百多年前一领天下的桐城文字,当文学大家们著作的时候,口里诵读的就是这样的语调。5018次列车,有桐城这一站。事情居然就出了变化。我那出身安庆的兄弟倒起来反对我到安庆去。他认为这个时候去有点贸然。他说,还不如一同去北京。脆弱!我居然就改变了方向,决定到北京去了。于是再去图书馆,还掉桐城派的书,转而借阅了不少关于清华大学的书。自从开始阅读陈寅恪以来,就对清华大学有了向往。到工字厅和新林院,成了我很迫切的所在。不可否认的是,抗战前清华国学院时期和抗战后回到清华詈目执教时期,是他学术生涯中最稳当的光景,大多数光耀的作品就成于在清华的这些年岁。抗战时的颠沛流离和文革时的朝不保夕,使得我们的国学大师默然承受了太多的损失和伤痛。然而,最深刻的作品却只能出于颠沛流离和朝不保夕!《柳如是别传》就在这样的艰辛之中诞生了。文化饱受摧残的境域往往能够压迫知识分子的良知,迫使他们积聚整个生命的全部力量凝结不朽的文字,发出最后的呼喊,慨然步向必然的消亡。家破国亡的时候,柳如是做到了;满目疮痍的时候,陈寅恪做到了。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气节。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到清华走走,能亲眼看到王国维先生墓志铭上的那两行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碑没有得以留存,但是心灵得到了我所希望的震惊。还有想去的是在天津的南开大学。恩来百年的时候,我填报过南开的志愿,可惜考分意外偏高反而错过了。由此便成了一份遗憾和一种芥蒂。所以准备特别留出一天的时间,往返天津,只为了到一到南开,了却心愿。朋友们都说,到天津你会失望,破旧的城区和生硬的话语。我不觉得异样。毕竟这是当时我冲动过,做好心理准备要在这里求学四年的地方。既然早就有了契合,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排斥。北京还有想去的是孔庙和国子监。不知道是为什么,想沾染点书生意气吧,将来能把书好好读成。呵呵。原来想去桐城,也寻思着能求点文气,写文章能够得心应手。是有那么点功利性。在北京,和兄弟准备做一番“地下游”,不去纪念馆博物馆不去名胜古迹,就在北京人生活角落里转。胡同、四合院、京片子、烤鸭、一二三四环路。也许到人艺去看场话剧,去什么屯的泡个吧,松松垮垮地把日子打发了。有时间都坐几趟北京的地铁。我还记得那一部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北京电影。周四下午休息的时候,我走了好一段冤枉路,在长乐路找到了的“汉学书店”。一半新书一半旧书。因为时间紧张,没有好好的寻觅。当时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有个老外在找书。那双蓝色的眼睛,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各色古文书的脊背上逡巡,没一点的困惑。还有书店老板全然不管顾客,单在和一个低年级大学生谈论今年复旦的录取分数线。老外走的时候和老板打了个招呼,“老板,我走了,以后再来”,普通话很标准。老板也很随意,点个头,“再会再会”,上海话,也没什么不自然。原来还是老客户。临走我买了两本书《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集,三联)《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王永兴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回到家,在《元白诗笺证稿》夹了张小纸条。“2004年8月19日,上海汉学书店。走了好长的冤枉路,终于买到了陈集中的一本,那么这路途即算是一种简单的朝圣吧。”也许可以在清华买下另几本陈集著作,甚至更有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