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605
- 积分
- 3733
- 威望
- 91
- 桐币
- 1307
- 激情
- 5602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92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8-1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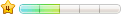
桐网举人

- 积分
- 3733
 鲜花( 5)  鸡蛋( 0)
|
本帖最后由 一璐福星 于 2011-8-6 15:22 编辑
0 F: k: i. k2 Z$ X; j" ?) q( e+ `$ @7 z" M. N9 |8 F1 c. S
——枞阳《童氏宗谱》收藏赏读8 Y6 z; `3 H* Q: ^& ]
6 s. A0 B l s, [, W
几年前,我偶尔收藏了数十本枞阳《童氏宗谱》,原以为,此类古籍体裁狭窄,内容枯燥,大多没有什么文物史料和欣赏收藏价值,但在经过翻阅和整理之后,我不仅对枞阳童姓源流有所了解,对古人的尊宗敬祖及家族观念深感敬佩,并且坚信,枞阳童氏即便不是什么王公贵族、达官名流,但也绝非泛泛之姓、平常人家。' k, ]) p5 i0 _
' |# Z- T5 J' h2 J8 Z) Q7 R 乡 贤 汇 聚 名 流 云 集
6 k: `% V0 v! r: \/ F
& M; {' i t. _8 d/ G 明洪武三年,也即公元一三七零年,大明朱氏江山甫定,为了休生养息,治理国家,朱元璋下旨户部,进行大明王朝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安庆府桐城县的一个叫“道土坂”的地方(今枞阳县境内),有一个叫童善庆的男子,他全家八口人,事产草房三间,所谓“户由”上不仅刊有由户部转发的圣旨原文,还有“安庆府提调官、知府赵好德、桐城县提调官、知县左彬”的落款,这个叫童善庆的男子,也即枞阳童氏四世祖。6 n: ~) |8 U. G3 d0 E
( K3 C, {0 g7 Y: s% D* U4 C5 h) M
资料显示,该姓宗谱初修于明末天启二年(1622),由“赐进士出身,詹事府协理府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待读学士”的何如宠和钱至立<万历诸生,钱澄之之父>作序,续修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由“赐进士及第、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起居注礼部尚书加二级”的张英作序。如果说何、张二相国等仅仅只是作了篇跋文的话,那么到嘉庆二十年(1815)三修和宣统元年(1909)五修时,则分别由姚鼐和戴鸿慈捉刀,并分别据其手书上版刻印<同冶十一年(1872)四修题跋吴廷栋,五修题跋另有姚永概等>,十分难得。特别是姚鼐在题写这篇跋文时已八十五岁高龄,这年也是他的忌年,因此很有可能是他的传世“绝笔” <见附图>。他们的题款分别为“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例晋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礼部仪制司主事、祠祭司员外郎、戊子科山东主考、庚寅科湖南主考、辛卯恩科会试同考官、壬辰会试提调官、充四库全书篡修官、嘉庆庚午重宴鹿鸣、钦加四品顶戴姚鼐”并置篆书“姚鼐之印”和“姬传”印各一方,其次为“诰授资政大夫、覃恩加一级、晋封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署户部左侍郎兼理钱法堂、总管三库事务”的吴廷栋和“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法部尚书、参予政务大臣戴鸿慈”,并篆印两方,之所以原文摘录先贤们自题的仕途经历,窃以为,它们较为真实可靠,或可勘误相关史料或弥其不足。为便于行文,凡为童氏某先祖作了传记的历代名人,也以大体时间为序,摘要作简单排列——
" v7 S4 }$ @( D+ P+ E 赐进士中宪大夫,江西按察使副使黄敏;
+ N) H L, N& ?% u0 Y$ {' j7 ]0 v0 h
/ m5 `7 `& N- L: N0 [( e 文林郎知安陆县事夏民怀;
. o& p4 p3 \6 n* V# l
, [& b" G1 s6 C- {! k r5 H, k 敕封文林郎,江西道监察御史方学渐作《辅仁会馆碑》碑文〈以下简称《碑文》〉及《定夫公传》,并附《江南通志》; d% x4 a, V/ D7 d
0 e" v) |4 u( A& _4 R 方大镇为赵鸿赐、童自澄作《高士传》;
2 O- `, |6 H4 o; ~3 V: b# s
* @& x5 V+ V4 P: l$ C/ l; R! i; V 钱至立为其表兄童一纯〈童氏十世祖,钱母为一纯姑母〉作;
% q! h& Q6 n: h) E: {: u4 q. d i' l. }/ y% g+ y/ u
万历丑仲春上浣之吉、桐城县儒学署教谕事、举人陈嘉酞;
( S; g$ e! C( w4 Q( n6 R- F3 ]2 H
& F& X3 u" n+ ?5 M+ y4 ~# v 三品衔湖北侯补道黄帮俊;" |& j! ~ Y8 Z1 D( v; n. Y2 M
0 m/ ~4 V) E3 o- _- u 钦加四品衔、特授铜陵县正堂杨绳藻;- c" I: O5 O. k" r$ M0 H" k
. x/ d* l/ r1 O! R$ l
钱澄之为其表兄童心铿作;% s* E0 }* Q- @! E5 p
8 ?( }& d! t5 H* v/ a# g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山东通省学政、按察使司佥事任塾;+ ?4 x9 s6 }7 [2 s& V9 Y9 ~
3 T* n' B2 G/ W* |+ G7 {1 E% z _ 乾隆丙午科举人、东流县教谕王灼,并篆印两方;- j# N: A f. @" Z1 r: r
& @- D) @ J: l
乾隆辛亥岁贡生、侯补训导吴中兰,篆印两方;
9 E2 U& }) `; W! ]
- s v" b3 ~" a0 o 诰授荣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闽浙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汪志伊,篆印两方;( c4 }) } e7 J8 q
" Q3 Z& F3 t) i& s Z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前任内阁中书、汉票签行走兼本衙门撰文加三级龙汝言,本人及“翰林修撰”篆印各一方;( G' M( ]8 \: b" l& H
/ d# X( d( E& C( _" z+ C p/ W/ Y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兼刑部山东清吏司加一级胡方朔,篆印两方;: m( I& h- {0 R- A8 U
7 d, k8 y, ?# \, ?9 k$ P7 Z3 n
敕封文林郎、知江苏松江府奉贤县事张敏求,篆印两方;
7 j$ e0 ]% g1 u: k' P* f
+ t5 u4 u: K( z( n* D: K( B 赐进士出身、特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陕西道监察御史、稽查工部钱法堂事务、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史科掌印给事中加四级、记录六次孙世昌;% `, m3 L% S, i% [/ A% E
. N1 e# K$ W9 t2 g5 l7 c 赐进士出身、苏州府教授孙起垣,篆印两方等。
/ v. v' |1 d3 U7 b X, X* M
) x! g4 C1 H; M4 X, q 理 学 泛 滥 会 馆 林 立
3 x/ B0 e9 ~1 s- f; {/ w
& ~+ A9 K. z1 _4 o' h9 q. Y+ W. I 枞阳,西周时为宗子国,西汉元封五年(前106)置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为同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又改为桐城县,一九四九年二月分桐城、桐庐两县,建国后改桐庐为湖东县,一九五五年更为枞阳县。有史以来,这里的青铜冶炼及青铜器特别是钱币的铸造较为发达,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这一带的经济却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文化事业也相对落后。据《桐城县志》记载:“明初桐城地属畿内,易得风气之先,县人竟相以读书为进取之阶,学风渐盛”。到明代中期,邑人何唐〈字宗尧,生卒年未详,正德进士,曾官至浙江按察使司提学副使、翰林修撰、兵部主事、郎中等〉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归里后以讲学为业,首开结社讲学之风。嘉靖、万历年间,一些学子或因屡试不第,或无意为官,在桐城县教谕张绪的影响下,以陈真晟、王汝止为榜样,经年研习孔孟之道、经世文章,并四处游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赵鸿赐、童自澄和方学渐,后来被尊称为“桐川三老”。赵鸿赐,字承元,生卒年未详,但据方大镇《高士传》记载,卒年七十三岁,其父赵代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后辞官讲学;童自澄:1529~1612年,字定夫,因指石为师,题斋曰“静”,人称“静斋先生”,童氏九世祖,虽“妻配丁氏万贯女”,但因交游四方讲学之士而家道中落,乃“而贫为学”;方学渐:1539~1615年,字达卿,号本庵,人称明善先生,有“布衣鸿儒”之誉。据《童氏宗谱》记载,赵鸿赐“畅然升其堂、跻其室,遂与同志之士为陋巷会”,并立“十二戒约(略)。童自澄立社于“永利寺古道巷,月三会其学,以“良知”为宗,前后历二十余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相与醵金卜地,于射蛟台下筑馆,曰辅仁”,是年,童自澄已六十四岁。- Y3 a! I, H, q* ^8 U! M
( _; m M2 N3 X( z" _
方学渐在《定夫公传》中说:“学渐频至其馆订正新知,定夫亦时来桐川相为枹鼓,尝惠书”,可见“辅仁”与“桐川”两会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在诸子百家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主要讲授性善之旨、经世之义,童自澄还在阳明学说及泰州学派中吸取营养,并首倡“心学”,一时学者如云,名流汇聚,学风大盛,致方园百余里百姓人家“贫不弃书”,诚为家训。《碑文》还记载,张英的曾祖父张淳为“辅仁会馆”题扁:“江滨邹鲁”,还有“司理周公曰:一乡善士;工部刘公曰:化行一乡;学台杨公曰:素行可风;抚台周公曰:高士。皆署扁于堂。致馈有差缙绅过枞阳,必临集,父老子弟而训迪之”,可见其盛。
5 a" a5 v" ?' v$ a$ F+ E
7 E. r) |1 _, o- X 十七世纪初,桐城至枞阳一带,先后还涌现出了如“泽园”、“枞川”、“金山”等众多讲学会所,此间同样以讲学为业的钱至立在《童氏宗谱》初修序中说“少时尝受业于定夫先生”,方大镇也在《高士传》中说“独契慕两先生,时时就正,两先生也以为孺子可教也,而小友友之,受益甚厚”,方大镇(1560~1629年),字君静,号鲁岳,方学渐之长子,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按、大理寺卿等,其弟方大铉官至户部主事,其女方维仪精研文史、工诗善画,其孙方以智更是名满天下,时人盛赞方式“一门五理学,三代六中书”——他们在汉学的基础上,提倡玄学与实学相结合,易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统一,这种折衷古今、汇通中外的全新理念,被人们誉之为“方式学派”,并且认为,其影响力仅次于孔门。虽未免有些夸张,但也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明未清初产生了较大影响,倘若不是满清入关,我中华民族或许会少走许多弯路,至少,自十七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段历史必然会被重新写来。
5 `+ W% h2 f' k5 p% w
2 V2 x+ ~+ e' Q9 ~1 Z, m5 c6 N0 {; `& u 当时,与“桐川三老”先后在世并时相往来的除《碑文》所记载的先贤之外,还有罗近溪、邹东郭、冯少虚、吕新吾、顾宪成、高景逸等,往后更出现了方以智、钱澄之、方孝标、戴名世、朱书,以及张英、张廷玉父子、方苞、刘大槐师徒等一大批文人学者,达官名流,到姚鼐时更是达到顶峰,史称“桐城文派”。; } r, x2 ]6 a# i3 X
0 D, h A, @; B. j; C
桃 李 不 言 下 自 成 蹊
: s S7 U |& U1 r; ?( t0 k T5 F& O: ?4 ` s) ~2 x2 H
明代中叶,稍早于“桐川三老”的正德、嘉靖年间,诞生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它的创始人是王阳明弟子,布衣王汝止,他继承并发扬了其师的“良知”之说和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实,所谓心学、方学渐在《碑文》中说:“枞阳辅仁会馆,童静斋先生讲学之所也。其地襟江带河,在桐邑之东百二十里,旧为县,陶土行尝为枞阳会。及县徙桐城而枞阳为镇,商贾辏聚……文学之士往往有之,而未闻所谓心学也”,由此可见,关于“心学”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既非程朱陆王,也不是布衣王艮,而是这位传道乡里的民间学者——童自澄先生。《碑文》中还引用童先生的话说:“余惟孔子之教,以仁为先,会子求仁以友,为辅仁者,人也。合天下为一人而后可语仁,故君子之当仁与天下共当之”,他的观点与王汝止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未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但说他们心高志大却也无可厚非。可惜童自澄先生无师自学,大器晚成,及至暮年又潜心治学、辅人,未及形成自已的理论基础。方学渐这样评价他:“静斋布衣而贫为教,不立文字,非有所震耀,驱迫也。唯一念真诚可贯金石。无论贤不肖,直提本心以醒之。用能浮于有众,枞阳之民半出门下,江之南北咸敬慕之”……
& d8 U7 V5 C- Y) r, p- H/ ?
3 V9 v7 v$ f' L* G 此外,据《定夫公传》记载,“邑侯会稽章公”、“豫章南昌黎公”等,常问政于定夫先生,并请他出山做官,先后历十五年之久,但先生均“固辞不允”,何如宠在《童氏宗谱》初修序中说:“记余童于时常游枞上,尔时枞有童定夫先生尝受教于明德罗公近溪之门,孜孜讲学于兹有年矣,比江南北数百里内诸人士翁然宗之,每会聚不下四、五百人”,童先生弟子钱至立及其子钱澄之也对先生多有评价,以为“学宗”。到明未清初,以钱澄之、方以智为代表的文人志士终以“文章诏后进”,戴名世、朱书、方苞等紧随其后,他们根据师承和家学,结合自已的个人观点,倡导“唐宋派”古文传统,反对八股文,方苞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义法”,被认为是“桐城文派”的开山鼻祖。他的弟子刘大槐秉承师学,并有所发展,姚鼐又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同时对各种文体都有一套具体的要求,他还把作品的艺术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终成“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其后如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人称姚门四杰〉、曾国藩、马其昶、林纾、严复等人,兴衰达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因方苞、刘大槐、姚鼐等代表人物均为桐城人,故称“桐城文派”,也称“桐城派”。' B8 D. ]$ [$ I( }# d4 o- K1 Z
2 H" Z: Z& ~" u& }9 D 宋、明以来,影响较大的除“八大家”之外,还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泰州学派次之,其实,所谓泰州学派,显然师承于阳明或浙东学派,阳明或浙东学派又源于汉文化或邹鲁文化,而汉文化或邹鲁文化却是殷文化、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的融汇、廷续和发展,它们各自既有衣钵的传承,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并且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体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 N a) q! K! |. i9 x' {6 E3 F! h7 `
- I( t9 p% Z: E. |' p! g6 e 毋庸置疑,世间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一个从源起到创立至兴盛再到衰落的必然过程,学术派别或者说“桐城派”也不例外,只是他们的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历史地位。如果说“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而“桐城派”又是颗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在方苞之前,必有人播下了“种子”、培好了土壤,并浇水、施肥,笔者认为,这些人应该是戴名世、钱澄之、方以智,应该是方学渐、童自澄、赵鸿赐,至少,倘若没有“桐城学派”,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桐城文派”。姚永概在《童氏宗谱》五修序中说得好:“余尝过枞阳拜童定夫先生祠,读家惜抱府君所书楹榜,概然相见吾邑学问渊源之所自……盖吾邑盛自前明,仕于朝者立气节,官于外则多循吏,居家则重理学,一时风尚然也。国初,钱田间、方密之二先生始于文章诏后进,学术稍变,然而立身行已、居家仍兢兢矣。笃守宋儒遗说,则又往者诸先生所留贻也,遗泽岂不长哉”……
; _; H! m+ _0 Y- ^$ E- d; h1 B# u* Y) ~6 K$ w# D
总之,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任何个人或者学派都难以驾驭或包容的,还是童自澄先生那句话,只要人人都以人为仁、以仁为人,不远的将来,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我中华民族都必将引领人类文明。9 i, \! B: z: ?: P5 C, Z0 c. L
8 P- C/ V, ~- ~' f) C3 l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