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79602
- 积分
- 1
- 威望
- 7
- 桐币
- 40
- 激情
- 16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0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2-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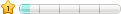
文都童生

- 积分
- 1
 鲜花( 0)  鸡蛋( 0)
|
你或许无法想象,是眼睛失去光明的博尔赫斯,让我决定要去桐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满东方和西方、世纪更迭、朝代兴亡的图书馆里,在无尽的黑夜里, 他阅读并写作。博尔赫斯,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记忆太多意味着什么,是在漫漫长夜里他无法入睡,白日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顽强地再现于他的头脑中,让他难安。但是如果没有记忆呢?就像青春期的我,对我们过去的历史一无所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生活仿佛是一场大梦,而最近3年,通过行走,我尝试将地理课本,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上的各种抽象地名、人名、片段一一变得具体而有温度,尝试丰富自己的记忆。
( u2 |. G/ x: p5 g# V* _, X1 L; S. N6 O# m1 _3 r
在桐城市老城里的大街小巷中我们转了很久,现在的桐城是一座普通得不行的县级市,城里的店铺一间连着一间,有意思和上岛咖啡这样的连锁店也在这里有了分支,街道上车流不息,随处可见各种商店牌匾和广告,城市的滨河广场是对全国各大城市广场的拙劣模仿,穿城的河流里看得见污染的痕迹,街市上的人们忙于商业和交易,搭载我们的出租司机大多沉默寡言,喧嚣的城市背景,让人感叹,明清时代的桐城人和现在一样吗?那个涌现出无数温文尔雅儒生,钟情诗歌散文和文人山水画的桐城,和今天的桐城真的有关联吗?" V! W2 F: n6 G# |1 ?
/ w) r. K+ l: O
只有进入桐城中学,感受校园里参天的大树,只有走进六尺巷附近的老城区,只有涉足那座优雅古拙的祭孔文庙,你才能稍微感觉到这里的与众不同。从汽车站出来,街道上的香樟树泛着新绿,但是火柴盒式样的房屋,规整的水泥路街道,让你怎么也无法想象,在十七、八世纪,这里个远离都市的小城竟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诞生于这里的桐城学派几乎是当时写作的标准和典范,这一派作家的行文和思想几乎塑造了当时人们思考和看问题的方式,方苞、刘大櫆、姚鼐是这种写作风范的肇启者,姚莹、吴汝纶、薛福成、严复、林纾都是这种该风范的忠实继承者。如果对西方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桐城的地位,大抵犹如十九世纪的北美的新英格兰,群闲毕集,爱默生和梭罗是当时的代表。但是新英格兰的爱默生尊崇超验主义,推崇想象力、梭罗崇尚个人主义和公民对政权的不服从,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政权的仆人,但桐城的学人大多终生考试,期待进入政权学优则仕,他们生活在一个千百年来压抑自由的集权社会里,对历史情有独钟的文人们对文字狱的严酷战心惊,自然,人们采取了妥协的方式,要么参加科举,要么教书,放弃对政治、社会的整体和深入批评和思考,躲入考据和形式主义的小世界,创造一个精致风雅的文艺世界。
6 w& w7 e3 p+ c# B
3 t; u3 G7 K1 v7 X4 v 来桐城之前,我在网上找了桐城派代表作家的作品,准备好好研读一翻,可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那些文言辞句,是中国人沁润了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文字丛林,我可以阅读梭罗和爱默生的英文原著,却对自己祖辈创造的文体感到力不从心。我的朋友跟我一样,对地中海文明更为钟情,我们可以讨论帕斯卡、蒙田和边沁,却对孔子、孟子、庄子的著作毫无兴趣。其实对文字和文化传统的背叛并非始于我们这一代,大约一百年前,距离桐城不远的胡适,陈独秀才是这种背叛的发起者,他们一个主张文学改良,一个主张革命,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那群知识份子,比如鲁迅,更是认为线装书都应该扔近茅房或烧掉,传统里写的都是“吃人”,更不要说晚近否定全部过去,沐浴着暴力和血腥的文化大革命了。
d' v. H' g! I0 L) S' J: f( m, B4 w$ E, D" i
晚期的桐城代表文人基本上都是洋务派,主张变革革新,姚莹凭借自己的地理著作跻身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严复和林纾则通过翻译运动给思维固化的国度引入了新的人文景观和思想,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和管理的京师大学堂本质上是对千年科举教育的否定,而薛福成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尊崇则是对中国道统和政治体制的忤逆。所有的一切,都令我感到那股士人浓烈的家国浓烈情感,它深藏于那一代最优秀的中国人身上,让他们即使在最为悲观的时刻,仍有行动的勇气,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俘虏。' O, M. H3 z6 n+ s" j% `
( p% ~0 B/ Y* U+ B& }
也不免想到推崇桐城文脉的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他们管理这个辽阔国家,要面对太平天国、捻军和革命派的崛起,也要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甚至近邻日本的挑战,在忙碌无尽的案牍工作后,但他们仍要抽出时间扮演他们喜欢扮演的角色——饮酒、吟诗,与文人朋友们感慨人生和历史的无常。他们开启维新变革,引入新世界的技术和思想,改革教育,外来文化的到来,引发了一连串变化,在词汇的革新之后,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革命便悄然发生了。
+ V. `4 E9 y! r1 m' t5 }' b6 r. q5 ?) e: T- n# ]; A. ~& l8 I' K+ l
退回到桐城的时代,那些温柔墨客们大多是县城和乡村出生的少年,他们是聪颖异常,也异常坚韧,在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度,人们很少有机会获得教育,而获得教育的人们,很少有人愿意在漫长的黑夜里,独自面对那个深邃的陌生世界,致力于书写自己的情感和忧虑,倾注所有的激情与创造力,然而,就像严复和他的追随者,从他们身上,你可以感觉到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哲学,坦然于自己在一个躁动世界悄然却充满韧性的努力,成为持灯的使者,给晦暗不明的世界带来光亮。
7 r6 x/ S4 l) a: Q7 p' N
* f- j& L7 O ~7 P6 \/ x" B1 y; @3 h$ X' k9 h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