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93376
- 积分
- 90
- 威望
- 0
- 桐币
- 10
- 激情
- 15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54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3-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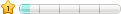
文都童生

- 积分
- 90
 鲜花( 0)  鸡蛋( 0)
|
薛家屯旧时暮春夏初小景
(2013-03-07早8点半绥化西门外)
1.
诗人们喜欢郊游,世人也喜欢的,比如清明或端午踏青,到老远的野外采青,拿一些青树枝回来,以示欣然。绥北诺敏河晚春,早是节气中的夏季了,不过还刚是春的味道,早春索然无味的,早春风景太单调。暮春了,招呼几个小伙伴去野外,说不清是玩耍,还是看风景,也许漫无目的最好。婆婆丁花黄了,它种子熟了飞满天。捉鱼吧,可沟渠里只有蝌蚪,还很小,地里也没啥子可吃的。唉,陌上谁家年少,空风流。
老牛吃嫩草,老牛最喜欢的了。“咩咩”的老羊也是,嫩草谁不欢喜呢。草色遥看近却无,不对,近看草色才浓烈着呢。田头一条小溪,似乎没多少水,老牛垂头,是喝水,还是孤芳自赏,尾巴悠悠然甚是从容,可非夏季,没得半只蚊虻。斜坡上,早春烧荒的灰痕还在,春日雨水小,冲刷不掉,或许要等青草满岸才能覆盖掉。一个繁盛的季节,似乎刚刚来临。远处,邻村谁家后园子一片娇艳,是农家果树开花了,春夏之交开花的肯定是李子树,李子花白的粉的一嘟噜一嘟噜,一树树胭脂的梨白。也许,轻碰树桠,清香,花瓣灼灼如雨。
小时候,我绝少到老远的地方,大都在村社四围转悠。春夏之交,山野好尴尬,好荒凉,但到处充满着契机,我才奔向山野。孩子时代就是有活力,跑了一整天,不知累,也不知满山野的瞧个啥。懵懂的年华好傻好傻。那年月,孩子都喜欢满野的奔忙,用铁夹子打山雀,成群结队的山雀似乎太傻了,在平原地带游荡了一冬还没够,似乎还要神游。要知道,山林子刚刚放叶吐青,还没得食物充饥。山雀子也不傻。山雀子野性,比麻雀好养活,孩子们都喜欢山雀,也都像山雀子。山雀子叫满柳条林的时候,孩子们随着杨花柳絮一溜烟的跑,跑遍青野,跑老了春光。暮春的清早,空中星子粒粒可数,晨雾蒙蒙,雾气深邃广袤,这样的大清早,鸟语啁啾。或许,鸟孩子,在听鸟妈妈讲故事,讲述如何捉的那条大青虫。
2.
此季,农事如山如海,也许,你一时愕然,“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确,红墙铁皮的大砖房住着舒坦,那是春夏劳作而来的呀。人和老牛比肩接踵,累日复年的劳动,耗费的气力难以筹计。如今,耕牛废用,农事似乎缺失了幽然古意。老石磨、石磙子、石碾子,那个“石头年代”一去不返了。当年,这些生产队时代的石器,分队后还曾一度使用,后来,终于被镇压器、小火磨、移动粉碎、电磨(甩渣机)替代了。之后,石器还可随处可见,成了多余的景致,而今,很少见之,不是被沉埋地下道旁,就是沉寂在谁家院角。一墩老磨盘,一块老石碑,一截老树疙瘩,一架小木桥,都沾满了如诗如画的回忆。
山野地里,农用小四轮背着犁杖,背着叫“铙钩”的犁杖(铙钩是绥北特有词汇),突突突突,响个不停,在趟地,趟二遍地。很早,司机很能起早吃辛苦,起着车,上山趟地(俺那把田地叫“山”)。一趟就是一小天,一趟就一个季节。俺那讲究三铲三趟,不趟地,地块就荒芜得侍弄不过来,趟地是最好的除草办法,还可给土地舒筋活血。土壤疏松了,根须扎的深,才苗壮。可惜,现在咋么趟,都无济于事,毕竟,土壤被化肥板结住了。板结的黑土地含不住雨水,下了雨,就一顺坡溜跑了。嘿嘿,土地也得了糖尿病不成,土地难道也得做透析么。鬼才知道!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农忙假放了,农村老师们也种地,也忙着侍候地。农村那片天,春季都是忙碌人。待到漫天柳絮不飞了,农事稍稍闲暇,朝阳渐上,清雨徐来,山野黛绿,庄稼长起来了,野草青起来了。山在长高,水在淌青,一个充满激情的夏日来了,一个蓬勃的青春期到了。夏天比春天更富于创造。夏日里,似乎所有的小动物,都忙着喂食,都在忙着哺乳后代。新陈代谢是万物的属性。农夫忙碌着,顶着夏日毒烈的太阳,在铲第三遍地。
平原上,每一个村子都是古村,百余岁的古村落。俺薛家屯也一百岁了,以在那定居最早的薛姓人家命名的,薛家屯。薛家屯是一座牛马羊群的村庄,这样的村社,松辽平原上,星罗棋布。大平原素来以牛耕闻名,庄稼人的心是牛肚,能吃能装。庄稼人的胃囊是牛肠,粗茶淡饭,五谷杂粮,通透直爽。农事其实是颗粒状的,一粒粒米粟繁殖万颗籽粒,一粒粒泥土垒砌窝堡村庄,一粒粒雪花填补老井水,一滴滴血汗收获天下粮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从陶渊明的田园诗,或许,一斑窥豹,可见农人的辛酸和快乐。
3.
我的小村,薛家屯,旧时候,没有富户豪门,自然就没深沟高垒,没有古宅高墙。但却有胡马,胡马自然是老毛子和小鬼子。也有胡子,闹过红胡子。俺那荒蛮,生长过土匪,也生长着抗联的故事。岁月成了历史,却空空如也,只是江山改了门庭。百姓如故,过着他们的日子,我的小村还叫薛家屯。当年那些老人故去,老故事成了绝响,岁月竟如此斑驳,最后,了无痕迹。小村角落的苍苔,年年累积年年绿,苔痕愈发幽然静谧,仿佛与我们隔了尘世。
初夏了,早晨,还有点小凉,小村里炊烟依旧升起的很早。一出门,便见邻家打开了鸡架门,撒出鸡鸭鹅,大公鸡威然踱步,鸡鸭鹅的叫声十分精美,是亲切的晨曲。农家生活栩栩如生,一点都不拿情造作,最朴实的也是最原始的,最底层的也是最天然的,这样的日子最平淡,也最有寓意,可见,平淡粗糙比精致含蓄更可爱。这才是文化,掉渣的文化说不准最润活。小村里有最大,最大的是填塞了的老井,还有那尊老石碾子,还有老校园的大操场。小村也有最小,母亲的针线,以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鸡毛蒜皮没小事。小事不小,大事不大,这才是平头百姓最从容的调子。
小村,小而简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早些年,村中村四周有好多大榆树,遮蔽了村子的半边天。那时,孩子们都巴望着树外面世界啥样,长大了,树木砍伐了,砍光了,四外不过如此。小村永远巴掌大的天。小村子很小,地图上简直没予标识出来,小村像一粒草籽,从跑马占荒岁月遗落,繁衍成今天的模样。小村像一颗颗黑糊糊的泥溜溜儿,俺那疙瘩以前玩的溜溜,土制的“玻璃球”,俗称“弹溜溜”。泥溜溜是孩子们集体的玩具,在父辈的手心团溜成世界(团溜,绥北方言,就是用手搓成球形),在我手掌里搓成人生。原来,小村子竟然托在农人的手心,他们血脉相连。村庄都是血肉之躯。
小村有自己的坟茔地,俗名“烂死岗gang3子”,那是村庄集体的祖坟,那葬着村庄的先人。俺那有村南十二坟地、西北沟坟地、东北小庙。其中,东北小庙坟茔地已消失十余年,是被邻近的农耕户挤占没了,当然,那些坟头没了户主照看,枯朽的棺材被掩埋作物下边,被塌陷的耕土填埋。有时候,趟地,犁头挑破了朽烂的棺材板,很厚的糟烂了的大红松板材,经年累月成了木渣渣。地下空壳的棺材尸骨荡然无存,这个情况是多年前,至少十七八年前,我在十二坟茔地见到的——道东,公路东侧那块坟地北头。原来,村庄命运如此,农夫们的命运如此。好悲凉,人世走一遭,来去都空空如也。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坟场,千万个坟场组成了另一个世界,那叫天国,那叫最朴实的老屋。天国也是一座屋子吧。
我爱喝酒,高度的头烧,65度,是农家烧锅(小酒作坊)提纯的头茬酒。然后,封口于坛子里,或在大玻璃罐泡上橙色好的草参,酒气清洌,来一碗,喝得两眼热淋淋的。然后,捶胸顿足,到雪地上打转疯跑,烧得心肝肺着了火。或者,干脆,摇摇晃晃,找个热闹场所乘兴侃大山,用独有的关东酒话,唠酒嗑。小村,被男人当作酒瓶子,揣在怀里,三九天焐热了。小村,被女人们当成一竿竹,晾衣裳,浆洗永远是农家的调子。
村庄的屋檐都不那么高耸,朝着大地,而非高瓦红墙四角飞翘。屋檐低小,也给了麻雀飞不高的缺陷么。但村庄的孩子飞得很高,念了高中,读了大学,毕业离家在外漂泊。还有一些人在外谋大事,都无非在努力改善着生存状况而已。漫天雪的季节,小村白了头,正如守着它的老人们鬓发苍然,正如守着它的大花猫,白了眉毛的老猫,慵懒的纹丝不动。老人和猫狗们都在晒太阳,是冷冬的晌午,在自家火炕上,时光暖而静切。日头透窗而入,炉火熹微,寒意皆散,这就是猫冬的日子,不宽不深不复杂。厚德载物的小村,村深小路接天涯,不论村民在外走多远,赚的如何钵满盂盈,如何的拥红叠翠,他都有个母土,到哪一提及籍贯,他就不加思索的答曰,薛家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