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 w. U$ X f2 m+ h' V
7 w. U$ X f2 m+ h' V
南通女师旧照
: {0 ?( F, a: F
5 m% K6 K" |3 t/ ~& d9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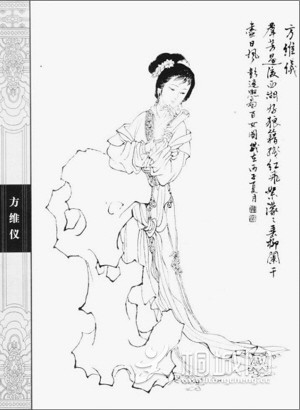
( M: ~+ ^3 Q7 q/ S2 f9 O方维仪画像3 Y$ b; f9 ?' p# Z- I1 f, `3 ]
8 z! g7 O6 l! X/ Y
 7 ^# j; b# E7 k& M( {, ^5 w$ G* q
7 ^# j; b# E7 k& M( {, ^5 w$ G* q
姚蕴素
8 W7 z- l$ U- A) o: E
7 }+ f- B" \% d( |: g-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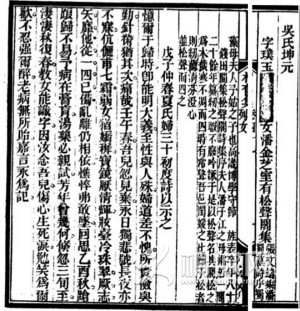
6 _7 V1 |/ H L/ i" H- B) N《桐旧集》里的吴坤元+ _6 t) _3 c* l
5 @* S# V# G( q3 H6 N1 x+ x: |桐城文章,一向以桐城派闻名于世,而在古文之外,桐城诗歌的成就,自唐朝曹松以后播名久远,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伴随桐城文学的异军突起,一批女性诗人提着优雅的裙裾,姿仪款款地走上诗歌舞台,她们或浅斟低唱,或壮怀豪逸,创作之浩繁为古今闺阁之罕见。乡人方于在编辑《桐城方氏诗辑》时,就抑不住自豪地赞叹:“彤管流徽,吾桐最盛”。今天的我们翻开那存世不多的诗卷,仍能从墨写的吟唱里感受家乡名媛的慧质兰心与精神气节。4 A* X( ]% `. \4 _& O
/ ]# o- K4 h( y, }. j0 x
清芬阁里的名媛结社
. G W4 d$ {9 G8 I桐城女诗人中成就最高、声望最著的,当推方维仪。方维仪(1585—1668)本名仲贤,字维仪,是大理寺少卿方大镇的次女,明末奇才方以智的二姑母。方维仪17岁嫁同乡姚孙,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她便回娘家守节于“清芬阁”。方以智出生于桐城县城凤仪里,自小受母亲吴令仪、姑母方维仪家学教导,尤其在12岁失恃以后,所学《礼记》《离骚》等尽出于姑母亲授。可以说,方以智日后能在文学、哲学、地理甚至自然科学上取得高出时人一等的巨大成就,都与方维仪的悉心教育密不可分。! p$ N% f$ L' U6 `* E5 }
" Z# u0 f7 O2 v* y6 }, ? A X! X方维仪一生洗尽铅华,归于质直,这段人生际遇集中体现在她的《清芬阁集》中。同样是国难家患,同样是人间死别,方维仪的身世遭遇与南宋词人李清照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她的诗文更多了一层学识胸襟的厚重。其诗又有明显的老杜遗骨,格调甚高,这在闺阁诗文中绝不多见。她的一首七律《病起》便是此中典范:9 K5 L4 b k8 s
空斋无事晚风前,雨过苔阶草色鲜。远岫云开舒翠髻,新荷池畔叠青钱。' ?, s1 t3 l3 ~" z! p0 \# N( g) I R
衰年转觉多愁日,薄命何须更问天。闲坐小窗初病起,西林皓月几回圆。
# F ]- v! Y1 q$ H% w/ F& z3 w3 L9 k4 P- M' P6 b8 C7 t& I
明末的文人名士素有结社的喜好,方以智和他的玩伴钱澄之、方文、孙临等,都是结社的“老玩家”,这种流行风俗也传播到了闺帷之内。方氏家族有了方维仪这位女中诗杰,必然辐射到一群志同道合的闺中才女,这就聚集形成了桐城境内最早的名媛诗社。他们的主要成员有:方以智的三位姑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其中孟式在其夫张秉文济南遇难后殉节大明湖,维仪、维则均是年轻丧夫,守节终老,享寿八十四,合称“方氏三节”。
f* Z0 N6 C! Z; } L3 Y/ b8 V; y
在名媛诗社唱和酬答的风气熏陶下,几位晚辈的闺阁翘楚,也都师承于清芬阁,将方氏一门的文学、气节发扬光大。代表人物有:以智妻潘翟、以智长女方御、中通妻陈舜英、中履妻张莹。方御记载了家中论诗的盛况:“当是时,姚祖姑居清芬阁中,余辈每就订正,争妍竞胜,不异举子态,悬甲乙于试官也”。以方以智为中心,且不论男丁,单是女性,他的姑、姨、母、妻、媳都是桐城名媛的中坚力量,她们的诗文更是这个传奇世家不可或缺的一缕翰墨清香。方氏一门文化,也由此步入鼎盛,无怪乎梁实秋认为桐城方氏,是“仅次于曲阜孔氏”的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
9 o5 L3 {- w6 g7 c5 o2 `! M3 Y% q6 _% i' S
名门闺秀的繁华锦簇1 @/ E- W5 _( t$ C/ h6 Z- a3 S
宋元之际,江西、徽州的大批移民迁入桐城,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多以耕读为业,家族在桐城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以张、姚、马、左、方、吴为代表的名门世家。他们或出仕治政或教化乡里,建立了桐城尚文、尊师重教的优良世风。方以智的曾祖方学渐,为明代大儒,他晚年于龙眠河畔筑桐川会馆,终使桐城学风一时蔚然。此后数百年间人才迭出,都赖桐川会馆建设学风之首功。3 f) ?2 L2 i5 h' G* D
% E& v1 C: q- ~桐城名门得以长盛不衰,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们不仅重视族中男子的文化科举,也同样重视女子的文学修养。朝代更迭的乱世中,男子为实现救国抱负纷纷离开家园告别妻儿,他们中的一些英雄甚至血洒疆场,留下弱媳在桐,使大家族对母教自然而然地重视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受教育的必然意义。他们自幼培养女子的诗文学识,又有名门联姻的传统,如此才能出现类似清芬阁结社的文化现象。在诗文的创作与鉴赏上,桐人给了女子与男子平等的地位,除了方维仪编写的《闺阁诗史》,尚有吴希庸、方林昌的《桐山名媛诗钞》、光铁夫的《安徽名媛诗词徵略》等专为闺阁诗词立传的著述。此外,潘江的《龙眠风雅》、徐的《桐旧集》,都为名媛诗词的收录、传世作出了较大贡献。$ [) {- O) y, p& e0 X9 S4 i) k6 v+ O! h
( {6 t* Y4 l; k9 D0 d以《桐旧集》的收录情况作为参考,桐城名门中闺秀立传较多的有:张姓9人,吴姓8人,姚姓7人,方姓7人。其中联姻关系也非常显著: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是翰林院编修吴应宾之女,“方氏三节”分别嫁张、吴、姚三家,张莹、张姒谊是老宰相张英堂妹,分别嫁方、姚二家,姚凤仪、姚凤姊妹均嫁方家,姚宛嫁张茂稷。这些名门才女中除了清芬阁五姐妹,还有一位较为突出的吴坤元。
: V; u8 b" _/ `+ K* Y. `# U/ D3 E4 T$ E+ d4 h/ Z( J1 P
吴坤元(1599-1679)字璞玉,与方以智同辈,是吴道谦之女,吴应宾的侄孙女,桐籍著名诗人潘江的母亲。她自幼聪慧,又受其从祖吴应宾的教导,成年嫁同邑潘金芝,不幸丈夫早逝,孀居二十余年。以《松声阁集》播有诗名,可惜受潘江《木崖集》禁毁牵连,也在几经焚毁后失其原貌。潘江正是幼承母教,博览群书,终成大器,并潜心采录桐乡前贤诗作辑为《龙眠风雅》正续集共计92卷,为桐城诗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6 d1 u" j# A5 w& a$ n- T
0 `. b7 x* |1 b" Y7 z
吴坤元的诗集学识与才思于一体,较喜用典,文字能于温和中见大气,于平实中见轻灵。她的《仲春送方婿井公之和州》是临行前送女婿方井的一首七律:/ j! m' M9 O6 x. h9 I
湖山烟水尚悠悠,岂是萧郎爱远游?却为刘犹下第,遂令王粲又登楼。
* O' M* p2 t$ ?$ ?0 E" H8 S8 B/ z* s+ M
) H& Y3 c& I" ]# g三春杨柳催行色,隔岸桃花莫系舟。屈指绛帷休暇日,可知少妇亦知愁。" Q+ A0 z( F# Z0 l" @2 S
诗中用刘下第、王粲登楼的典故,鼓励女婿要有为国为民、不阿权贵的襟怀与气节。至颈联转而代女儿叮嘱“路边的野花不要踩”,不忍见女儿独守空闺愁郁度日,却又别具一番女儿情趣。身为长辈的期许与宠爱之心,都自然流露在诗句之间。从诗文特色上看,吴坤元虽也经历丧夫之痛,但语言多豁达,少悲戚,是其性情可贵处。
; b* \7 W6 X s; j2 z4 Q/ L( @
) M, ~; b K4 P1 P: G3 Y, ]# S姻亲成就的乱世佳人
# T0 A }) ?. S! ~. L" H) _除了本土家族之间的儿女联姻,桐城名门也与外地望族多次喜缔良缘。在那段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里,才子佳人们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红尘故事。% F5 I( {4 L; b0 H5 t6 y3 o/ r- ]
章有湘(?-1672),字玉筐,号橘隐,为华亭(今上海松江区)章简(一作旷)次女,桐城“神童”孙中麟继室。她幼时即有才名,在家中与姊妹章有淑、章有渭、章有闲、章有澄、章有弘被称为节愍章简公的“六朵金花”。孙中麟旅居华亭时,与当地名士交游唱和,人品学术也受到章简兄弟赏识,便以有湘许之。章有湘随孙返桐后,与夫婿有过一段琴瑟和鸣的甜蜜时光。顺治十二年(1655),孙中麟在殿试中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不料喜讯未及传回家乡,中麟就不幸身染恶疾,客死京城。章有湘惊闻噩耗,实在承受不了这番打击,数次自缢未果,从此为亡夫守节十七年,直至泪尽病殁。她在余生整理亡夫遗作,又自著《澄心堂集》等,与方维仪、吴坤元,并举为“桐城三才女”。
* B% B, A8 e6 K; D
8 p! O+ R; |: x$ [% e经历人生骇变,章有湘的诗词多写忧伤哀怨之音,或表告亡夫“与君不共齐眉案,纸阁芦帘瘗孟光”(《哭夫子》)的忠贞,读来令人悲戚扼腕。她的《浣溪沙·旅怀》用一种纠结跌宕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思乡之情:5 z( A4 _/ i% _" A
此夜难分怨晓钟,梦魂偏又到吴淞,愁情先上两眉峰。
8 m% X, q" J& N7 c6 M$ x沧海一声临远道,兰桡千里破长风,可怜回首隔江东。
. S8 Y% p8 o6 I- v2 [" f4 D' ~! K2 ^7 H( q0 y
陈舜英字佩玉,江苏溧阳人,是名宦陈名夏第三女,顺治八年(1651)嫁方以智次子中通。她自幼喜读书,性至孝,深明大义,有《文阁诗集》。其时方以智遁迹岭表,妻潘翟万里追寻,陈舜英放弃了娘家所遗产业,鬻钗钏迎姑归桐,为乡里称颂。中通数染沉疴,陈舜英刲股入药为丈夫医治。“粤难”时中通欲以死为父亲辩诬,陈佩一刀与夫共生死,并作诗明志:6 a* @. H# n, _/ Q2 |
世外犹遭难,人间敢惜生?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
" @2 }! L* J% O3 U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声。( t+ S Q* B5 L9 f% ?0 i. e4 Q
这般气魄从容的闺阁气节,早已超出其父名夏,惟桐城方家独有!
8 @% I$ L0 h0 o* K- U& N
3 _, R& c5 `) b当然,桐城作为诗礼簪缨之乡,受此文章学风的熏陶,不仅娶进来的媳妇各有巾帼奇志,嫁出去的女儿也都是脂粉英雄,其中最为著名的应数姚蕴素(1864-1938),字倚云,是名宦姚莹的孙女,清末桐城派名儒姚永朴之妹,永概之姊。在吴汝纶用心良苦的牵媒拉线下,姚倚云嫁给南通范伯子为继室,成就了一段姻缘佳话。姚倚云诗词能扬桐城一脉遗风,著有《蕴素轩集》,后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女教育家,并应张謇邀请担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首任校长,将桐城文化精神带到外地继续传承光大。
& T- b8 Z9 o' j9 Y# S7 |1 I3 o1 d' _
: x$ Z" B) l- F1 o! ~0 C+ u1 S据现有可查的史料统计,明清两代桐城有名姓记录的女诗人共160余人,得以传世的诗词作品近千首,创作之盛甲居安徽诸县。桐城人重礼、重教,处世存风骨,歌诗留气节,才得以扬桐城文化数百年之昌盛。名媛才女以优秀的诗歌谱写她们独特的人格风华,在文学的舞台留下绚烂不朽的传奇。4 W: p3 Y; S! o! I
; X2 }& V" S O% {; T# e. ^
来源:安庆晚报 作者:姚蕴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