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3868
- 积分
- 315
- 威望
- 2144
- 桐币
- 160
- 激情
- -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47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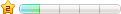
文都秀才

- 积分
- 315
 鲜花( 0)  鸡蛋( 0)
|
姚清芬和方维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一个人有两个名号,这不足为奇。奇的是她有两个姓氏。其实这也不足为奇,这两个姓氏,一个是她娘家姓氏,一个是她夫家姓氏。. U1 Q- H# v8 ~9 H
9 s$ D8 C3 |6 ]* r 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明桐城人。著名女诗人、书画家。方以智的二姑母。
1 d/ g) G! Y4 A 3 j( H/ l& T, c+ {5 z. {& R* L
明末的桐城方家,已是赫赫大族。著名学者方学渐,方维仪的祖父即方以智的曾祖父,读经治史,习《礼》研《易》,著书立说,游走四方,讲学终身。他曾在著名的东林书院讲学,并在桐城创办桐川会馆,开桐城设馆讲学之先河。学渐生三子:大镇、大铉、大钦,皆传家学,考取功名,其中大镇官至大理寺少卿,属九卿之列了。方大镇即是方维仪之父、方以智之祖。大镇生一子二女:长女乃张秉文之妻方如耀;次女方维仪;幼子方孔,方以智父也。
3 r5 y! \9 q" N # J( ]/ N, B' r5 Z
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学风浓盛,不独男儿治学,女子亦然。方家二女皆工诗善绘,经史在胸,不让须眉。大姐方如耀嫁了才貌双全的张秉文,二姐方维仪却没那么好命。她17岁嫁给表兄姚孙时,孙已是久病缠身,不足一年,便呜呼哀哉。丈夫死后,维仪生下一女,不足一岁,又遭殇殂。一个大家闺秀,年轻寡妇,自此重归娘家,守节终身。
5 U; R C- a1 c8 c , X5 T( {& h' ^# f% y7 M5 G. g
关于她的凄凉身世,她有一篇《未亡人微生述》,写得呼天抢地、如诉如泣:“余年十七归夫子,夫子善病已六年……明年五月,夫子疾发……至九月大渐,伤痛呼天……遗腹存身,未敢殉死;不意生女,抚九月而又殂。天乎!天乎!一脉不留,形单何倚?”丈夫和女儿都死了,公公在福建做官,婆婆也随在官署,她一个年轻寡妇如何在夫家长住?风言风语是难免的,她以诗言志:“翁姑在七闽,夫婿别三秋。妾命苟如此,如此复何求?泰山其可颓,此志不可劂。重义天壤间,寸心皎日月。”从此“复归父母家,稍延残喘。叨蒙父、弟友于,使无冻馁颠沛之蹶。”守节是要有资本的,在封建社会,女子嫁人不过是为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虽然寡妇守节被大加宣扬,但真守起来却也是难上加难的。夫家不留,娘家不收的情况多的是。所以也就只好背着失节的骂名,去改嫁他人,不过是寻个穿衣吃饭的去处而已。$ v; F; U+ U3 ]0 o
7 c+ A' y d/ ]1 ?7 c% K6 [7 k
方家是大家世族,当然不缺她的吃穿用度,这才能成全她“重义天壤间,寸心皎日月”的泰山之志。* b7 o9 ]8 o# w a; h/ K
人们往往喜欢拿现如今的道德标准来批评古代女子的节烈观,我大不以为然。试想一个男人抛家弃子去争权夺势,受封旌表,便是建功立业,可赞可叹的。一个被社会责任排除在外的女子,她能怎样?她要争的不也就是时代赋予她的荣誉吗?那荣誉就是贤良淑德,守贞守节。
$ [0 p$ K. E( i# f8 D4 ~! v; _ 3 ~% X0 u7 m$ x1 r' y u
其实回归后的方维仪并不是活得凄凄惨惨,窝窝囊囊的。相反,她活得自由自在,有尊有严。“弟妻吴宜人愉惋同保,不幸早世,余抚其诸英,训诲成立,完其婚嫁,必当终于一诺也。”这说的是她的弟妻,也即方以智之母吴令仪,与她情同姐妹,年仅三十便去世,留下以智兄妹五人,全由维仪代为抚育成人。) h. Q( P5 \8 n Y" ?
9 _3 w, D/ ~# y+ f 方以智12岁丧母,最小的弟弟才2岁。方维仪不仅像母亲一样抚育他们,还亲自教授学问:《桐城方氏诗辑》中载:方维仪“教其侄以智,俨如人师。”方以智自己则这样描述:“智十二丧母,为姑所托。《礼记》、《离骚》,皆姑授也。”, w7 M% z) |# c# B6 J7 p
+ T& }* q! Y% Z) a 除了帮忙父兄持家,抚育侄儿侄女外,方维仪还写诗作画,研史治学。她起诗社名《清芬阁》,与姐姐方如耀的《纫兰阁》、堂妹方维则的《抚松阁》互相唱和,史称三阁为桐城最早的名媛诗社。三方除会作诗外,还善绘画。她们的诗画水平之高,一点不在桐城的须眉才子之下。
% o0 U/ E6 z ] v3 U* k S8 E: H* B
9 m6 e% D2 L4 S) Q& n! [1 I1 a 方如耀有《纫兰阁集》十二卷、方维仪有《清芬阁集》七卷,均载入《明史·艺文志》。方维仪还曾编纂《宫闱诗史》,点评古今女性诗作。而后人点评历朝历代的女诗人,也必要提到方维仪,说她诗近孟郊,画不逊于李公麟。
8 z8 d) Z6 X$ T" X & G. h" E# `4 u9 Z
方维仪遭逢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乱世战火,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同样不幸。姐姐姐夫为国捐躯,爱侄方以智为反清复明奔走逃亡。方维仪的诗作虽不乏细腻多情的个人命过之叹,但更多的则是关注民生感怀时政的激昂悲壮之作。8 l! @. T2 L1 h7 G8 s% S6 w+ n
R% M; Z6 C# z+ |) }( q 感叹个人命运的代表作有《别离》:“昔闻生离别,不闻死别离。无论生与死,我独身当之。北风吹枯叶,日夜为我悲。上视沧浪天,下无黄口儿。人生不如死,父母泣相持。黄鸟各东西,秋草亦参差。余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日日复如此,我心徒自知。”( H6 R) s* q7 C! j1 N! H) l# C- g% ?6 J6 V
: c3 ~% ]. J' e' G 关注民生时政的代表作有《旅夜闻寇》:“蟋蟀吟秋户,凉风起暮山。衰年逢世乱,故国几时还。盗贼侵南甸,军书下北关。生民涂炭尽,积血染刀环。”5 r0 A6 V% E* ]% I; \
9 X! c9 k4 K4 ]) p) x1 a& K
她的代表作还有《拟谥述》、《楚江吟》、《归来叹》、《老将行》、《从军行》等。
9 J/ r; u- \ B- a
9 T. d( r8 \- I ] 方以智为其《清芬阁集》题跋时感叹:“嗟夫!女子能著书若吾姑母者,岂非大丈夫哉!”
& K, m& @. y% R6 U y, Z% G3 c
7 W. ?' G- S( J) c- s1 o- i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个女人的身影?方维仪跃然其间。中国的女性,入史册者,大多是以某某夫人寄名。历史上的中国女人,无法去与男人争功名,争的只是诰命夫人的品级。而方维仪,历史很慷慨的给了她一席之地。无须借助夫家,她是以自己的才学安身立命,留名青史的。
1 i2 u8 Q8 q# |9 u# a; }* P' n
+ g! a1 |0 K) M/ o; a 史书载她,或曰方维仪,或曰姚清芬。那个早逝的姚孙棨之名,反而是因为附在她的后面才得以载诸史册,留诸后世的。
; y4 t0 y! j+ G, |' \: y$ v, B- M ( a. i1 a3 @# o6 M5 Q/ h4 {
方维仪,小女子,大丈夫,一生坎坷,名节高标。84岁寿终。死后有专祠奉祀,祠中匾曰:“今之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