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6289
- 积分
- 2595
- 威望
- 24024
- 桐币
- 6644
- 激情
- 1276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21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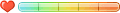
桐网嘉宾
 
- 积分
- 2595

 鲜花( 6)  鸡蛋( 0)
|
|
关于《水浒》与《金瓶梅》故事重合点的情景变迁
张庆
我们知道,《金瓶梅》的创作,始于《水浒》传世之后,而它情节的导出部分,实际上也是从《水浒》的一条支线上演变过来的。武松仇杀仇杀西门庆的初次失效,使得兰陵笑笑生有机会安排出这样的一段时间,让西门庆在偎红依翠中再享了几年的艳福,并拉长为一部整百回的小说故事。然而,需要明确注意的,笑笑生在武松拳下救下西门庆并增他几年阳寿的同时,也曾对《水浒》的其它细节,作过必要的调整。如果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些细节的调整,或许我们会错过很多重要的思考辨析。于是我有意在这里整理出四条极有深意的歧变现象,而对另一些暂时认为无关紧要的改写(例如阳谷县与清河县的地名反窜等)权且回避,局限于浅陋识见来试说一二而已。
一、潘金莲身世的改造
在《水浒》中,作者对潘金莲的身世是有如此安排的: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不会风流。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
这样的描述,使潘金莲在骤然之间,由一个拒从大户的贞烈使女,摇身一变倒成了“爱偷汉子”的浪妇。从这一点上来看《水浒》作者对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形象构造,很明显是欠妥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前后相悖的。而《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逻辑的不通,于是给出了他的新设计。在绣像本中,作者对潘金莲的身世来历颇费了几大段的描述文字:
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他父亲死了,做娘的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闲常又教他读书写字。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到十五岁的时节,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与玉莲同时进门。大户教他习学弹唱,金莲原自会的,甚是省力。金莲学琵琶,玉莲学筝,这两个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二人,与他金银首饰装束身子。后日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张大户每要收他,只碍主家婆厉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度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
当然后面的文字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陈列,无非是通奸之事败露,张大户迫于主家婆的压力只好将金莲许配给临街房居住的武大郎,而且也是倒赔房奁。但大户如此动机的目的还是为了与金莲“藕断丝连”,于是趁武大不在家时时常光顾,“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然而这张大户毕竟上了年纪,又没太厚的艳福,于是干脆“得患阴寒病症,呜呼死了”。这样一来更着恼了主家婆,便一气之下,命人把长久寄居在此的武大与金莲,一并赶走了。“武大故此遂寻了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而此后潘金莲对于这场婚姻的态度,也就愈发明朗起来:
原来这金莲自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犭衰),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抱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口床)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悄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
词话本在这一节里面的设置,与绣像本是基本一致的。潘金莲已经不再是《水浒》中拒从大户的“节女”,而是自幼便被卖出习学弹唱、惯会做致乔样、甚至被卖入大户家后一有机会便与“老刘郎”有染的风骚少女,那么她嫁与武大后依旧与老情人私交以及再往后主动勾引“浮浪子弟”等等情节也自然都在情理之中。就这样,《金瓶梅》的作者通过对《水浒》原文的这样一番改动,就顺理成章地安排了潘金莲在后文所扮演的“荡妇”的角色。而词话本更是点醒“为头的一件,好偷汉子”。
二、武氏兄弟之间关系的微妙差距
既然说是“微妙”,那么这份差距,就不是那么“显眼”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先看《水浒》中第二十三回,宋江初见武松时,武松便说“今欲正要回乡去寻哥哥,不想染患疟疾,不能够动身回去”,随后一段开头又是这样写的:
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武松道:“小弟的哥哥多时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
就这样武松踏上了回乡探兄之路。结果在景阳冈打死猛虎,受阳谷知县的盛情充任步兵都头。武松还曾暗想“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于是回末有语“又过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县前来闲玩”一段,这才是意外的巧合间与兄长相见,而武松的第一反应则是“扑翻身便拜”。从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相信武松此番回乡,诚然是思兄心切,而且内心也是极为尊重兄长的。然而,这些人物转接到《金瓶梅》当中后,这一情境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绣像本第一回的回目名取得很特别: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冷遇”二字,不由得令人触目惊心。从一开始,武松返乡的原意,就只是从一个外人应伯爵闲传中以“先前怎的避难在柴大官人庄上,后来怎的害起病来,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寻他哥哥”几句话中敷衍了事。后来武二郎充任清河县都头一职,也只用平铺的手法叙说“正要回阳谷县去抓寻哥哥,不料又在清河县做了都头,却也欢喜”,淡淡带过。而接下来与兄长的相见,正是不同寻常了:
却说武松一日在街上闲行,只听背后一人叫道:“兄弟,知县相公抬举你做了巡捕都头,怎不看顾我!”武松回头见了这人,不觉的欣从额角眉边出,喜逐欢容笑口开。
固然仍有“欣”与“喜”,但相较于《水浒》中的情态来看,已经不知寡淡了多少滋味!且重看《水浒》,在时间设定上设置说“又过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县前来闲玩”,这是值得理解的。起码在给予读者的印象中,武松是欲回乡看望兄长,因为打虎情节又临时受命都头,几下子折腾才耽搁了行程,这一次“走出县前”,可能也是偶然得闲的原因了。武大见其弟时便在背后叫嚷“武都头,你今日发迹了,如何不看觑我则个?”这明显是毫不见外且有意识的“客套”语句,因为连武大在见面后劈面给弟弟的话就是“又怨你又想你”。而武松呢?一听到这叫嚷声回头,便惊问“阿呀!你如何却在这里?”这惊诧的语气,也说明了他委实不知兄长已经迁至此处,这一惊之中又饱含了多少喜出望外之意。随后便是“扑翻身便拜”,却更见兄弟情浓了。
然后这一切搬进《金瓶梅》时都完全变了味。武松充任都头,似乎把探兄的初衷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却说武松一日在街上闲行”,只此一句与“又过了三二日”相比,不知在时间上给人感觉是漫长了多少。直到在闲行中被其兄发现,便在后面叫道“兄弟,知县相公抬举你做了巡捕都头,怎不看顾我!”这里面的亲情元素,也可以大打折扣了。尤其“抬举”二字,用得是如此艰涩,让人感觉有些贬损的意思,“怎不看顾我”这样的发问,明显是站在长兄的架子上,责问弟弟的“失礼”处。而武松这样一个“热血心肠”的汉子,在意外中遇见本要寻访的哥哥时,反应倒也如此平静,就难怪作者在回目名上就用“冷遇”二字了。
词话本第一回的回目名称“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在内容上也与绣像本颇多出入。从文字的表达与细情的传递上,似不及绣像本,因此这里不多细表。但词话本在刻写武氏兄弟的见面时,更是只以“武松回头,见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请家中,让至楼上坐”数句,寥寥带过。而这一待遇,与平常的宾客相见,也没有几分差异了。
事实上,不止在见面的场合发生了这个的歧异。在这一整场的见面过程中,这一歧变是始终进行着。在武大家中聊过话用过餐之后,武二就站起身来意欲告别。这时候,《水浒》中在这样的一段告别话语:
都送下楼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搬来家里住。若是叔叔不搬来时,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武大道:“大嫂说的是。二哥,你便搬来,也教我争口气。”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
潘金莲提议要求武松搬到家里来住,显然有她的一番私意。但这一点于情于理,也都是极恰当的,因此这个时候老实本分的武大也在一边怂恿武松,武松便依了“哥哥、嫂嫂”的盛情,答应搬来。但这一情节插入《金瓶梅》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字句调整:
都送下楼来。出的门外,妇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来家里住,若是不搬来,俺两口子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来。”妇人道:“奴这里等候哩!”
这样一个调整,便使得武大在这种场合下完全被“悬空”了。从头到尾他没有任何发言,这对于他这个名义上的“一家之长”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也就是说,他压根儿没有提出让武松搬到家来的主张甚至在妻子提出之后也未发表任何支持的意见。“与我们争口气”的话语,从原本的武大之口而转至金莲之口了。而武松也是一个“识相”的人,在这里既然答应了搬过来,但也只在言语中感谢了“嫂嫂厚意”,而对兄长就干脆一语不涉了。这里面,又究竟藏有怎样的文章?我们未必能够猜度得一清二楚,但如果我们再去理解一下第三个方面的改动,或许可以有所启发了。
三、武二与潘金莲之间关系的微妙差距
这个“微妙”,又究竟体现在何处?我们还是只能通过间或的细小文字差异,来观察审清这件事物的本身。
最显眼的一处,是《水浒》中武松初至兄长家时,作者曾借武二的眼光,来详细描述过潘金莲的造型:
武松看那妇人时,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这一段精细的描述,是由武二的视角来给予刻画的,这可见武二当时面对这位嫂子潘金莲,观察得是何等细致而又有耐心。但在《金瓶梅》中,这段精彩文字很轻易地被抹去了,而换成极平静的一小段:
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
这一处删简,其实是极值得推敲的一处:“十分妖娆”,这是一个极度潦草的形容,而武松就这样草草扫视一眼潘金莲之后,就赶紧把头低下,又是何故?说得更简单一些,那就是这里面的武松,绝没有《水浒》英雄形象里的那般单纯与坦然。如果他不是内心的“波澜”,又何必将头低下而不敢正眼相见呢?家嫂毕竟也是家里人了,他的这一举动,无非暴露了自己心里的不安宁。
不仅如此,在后来的饭桌之上,《水浒》中是这样的描写:“那妇人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这一处《金瓶梅》是几乎照抄的,但是绣像本在这里却又把末句“不恁么理会”删去了。那么既然“只低了头”,后面的余地又要大得多了。因为之前武二与这位嫂子在闲聊时,也就是“只把头来低着的”。这样的删改,无非是在武二与金莲之间,平添了一层张力。
《水浒》在这场家宴散去后,有一首简单的七言绝句:
叔嫂通言礼禁严,手援须识是从权。
英雄只念连枝树,淫妇偏思并蒂莲。
而《金瓶梅》将这首七绝作了大幅改造后,插在了这场相聚的中间位置:
叔嫂萍踪得偶逢,娇娆偏逞秀仪容。
私心便欲成欢会,暗把邪言钓武松。
这两首在文字上的改造是很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的后两句。前一首在后两句中以对比的句式,明确点出了“英雄只念连枝树”的立场,而“淫妇偏思”就是潘金莲的“一厢情愿”了。但在《金瓶梅》的文本中,在这里却只点明了潘金莲的意图“欲成欢会”以及在此意旨下“暗把邪言钓武松”的举止,武松的态度乍然未见。这岂不是有意回避了对武松立场的明确表达么?
然而武松也是真的并不单纯。在搬入武大家后,武大自然每天赶着出门卖炊饼,妇人则有足够的时间在家“欢天喜地伏侍武松”,而且还“时常把些言语来拨他”。面对这样的“撩拨”,《水浒》中表达武松的立场是“武松是个硬心直汉,却不见怪”,而改入《金瓶梅》当中,末后的四字“却不见怪”却同样被删除了。这样,武松只是“硬心直汉”,但心里是否有“见怪”的嫌疑,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一个跑荡江湖多年的人,当真会有明事理到如此地步么?相信此时的武松,早已经参透几分了。他之所以表现得无动于衷,或许只是因为他需要维持自己“硬”与“直”的性格特点罢了。
四、武松形象的歧变
对于这样三点的比较总结,或许有许多人会因为既有的主张,而不愿意予以接受。事实上,《水浒》是《水浒》,而《金瓶梅》则是《金瓶梅》,这两者本身就是两部而且两样的小说。其人物的形象也注定不可能是对等的。在《水浒》中,作者一心把武松创作成他内心当中最典型的英雄形象之一,但在《金瓶梅》当中,作者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在意所谓“英雄”形象的刻画,至少是对这一形象并不抱十分的肯定态度。这可以从其它另一些环节中更多地体现出来。
在武大死后,武松急于寻西门庆报仇,情绪显得极其狂躁。而这也正好导致了后来对李皂隶的“误打”,虽然是“误打”,却也最终导致了一条人命。而这条人命“晦气”致死的真实原因,不能不说明武松颇有些“杀人不眨眼”的盗匪色彩。这也难怪在吴月娘得知武松要与潘金莲成功之后,就明白地断定金莲“往后死在他小叔子手里罢了”。而这场血腥的“婚礼”,恐怕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残忍得多:
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剥净了,跪在灵桌上面。
那妇人见势头不好,才待大叫。被武松向炉内挝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来了。然后劈脑揪翻在地。那妇人挣扎,把髻簪环都滚落了。武松恐怕他挣扎,先用油靴只顾踢他肋肢。后用两只脚踏他两只胳膊,便道:“淫妇,自说伶俐。不知你怎么生着,我试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摊开他胸脯,说时迟,那时快,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武松口拎着刀子,双手去斡开他胸脯,扑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后方一刀割下头来。血流满地。迎儿小女在旁看见,虎的只掩了脸。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
本来就只是一件为兄报仇的事情,武松却如此残忍地表现了出来。这一情节,《金瓶梅》在借鉴《水浒》之后,将之进行了更多的放大工作。刻画得如此淋漓,竟至于令人不堪一读!也难怪作者形容到此,也禁不住收住笔,叫一声“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这样的话语了。
迎儿是武大前妻留下的一女,在《水浒》中不存在的角色,却是《金瓶梅》中的新添。这一角色在全文中实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但却是武松性情的另一见证。极令人感觉蹊跷的是,武松诚然是在为兄报仇,但对其兄长遗留的这个寡女,从未有过任何留恋与眷顾。在那一场血腥腥的屠杀当中,迎儿在一旁颤抖不已,也曾叫出一句“叔叔,我害怕”的求助信号。然而此时的武松竟然只抛下了一句“孩儿,我顾不得你了”,不仅没有中止自己这场盲目强化了的“复仇”行动,而且在此后扬长而去,压根儿没有为这个孤女留下任何生活的安排。直到事后陈敬济来寻金莲时,才由识熟朋友杨二郎的口中一并获知了这个可怜孩子的下落:“昨日他叔叔杀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将此女县中领出,嫁与人为妻小去了。”可见,武松对于这个与他有着绝对血缘关系的孤女,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亲人心态。我们假想这个女孩儿万一改作潘金莲的所生,那么她可能也要在这场血腥之中香消玉殒了。一个水泊梁山的情义汉子,就在《金瓶梅》作者的几处笔墨下,俨然变成了一个不通亲情的近乎“恶徒”的角色。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在《金瓶梅》中“杀嫂”的根本动机,或者有待更细的商量了。最起码,这个动机应该不会只是“祭兄”这般单纯。
总之,由于两位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不同思想指导,促使了这两部小说在故事的遗传重合点上看似微小实又巨大的变异处。《水浒》无疑是要依据建立并维护着作者理解中的大英雄主义,而《金瓶梅》则完全抛弃了这些所谓的英雄主义,以一种不屑的眼光给予鲜明的摒弃,并将揭露的矛头直接指向社会人的本性之中。应该说,《金瓶梅》当中的人物造型,其实更接近于我们现实社会的。欣欣子在为《金瓶梅词话》作序之时,开头即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世俗,盖有谓也”。是真言语。而廿公的跋语,则是更值得世人明醒注重的: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小说的创作,固然不如《红楼梦》《水浒》等作品那般或典雅或庄重,但它至少是一部有所思考有所启发的文字巨著。不以秽淫而轻薄,不以露骨而骄躁,这样的读者,才是一位真正健康的读者。
天涯浪子,戊子晚秋,于苦茗居。
[ 本帖最后由 觞客子 于 2008-10-4 22:08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