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6289
- 积分
- 2595
- 威望
- 24024
- 桐币
- 6644
- 激情
- 1276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21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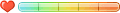
桐网嘉宾
 
- 积分
- 2595

 鲜花( 6)  鸡蛋( 0)
|
本帖最后由 觞客子 于 2009-9-19 14:37 编辑 " J$ w4 F2 |4 P8 Q- r
: C) B8 f( v7 o2 S5 z" f) |& A% z不可以小说手段证信史 & V/ m. v' Q8 G, E8 A
——重议方孝标兼与白梦女士商榷
0 D/ v) ^* g0 W1 \/ b 前段时间,有友人来向我推荐白梦女士的新作《迷雾团团的方家父子》,因受俗务匆忙竟在一时腾不出太多精力,延至今日方得初窥大略。心中有若干想法,不能细翻资料来一一明细,但有几点意见,欲藉此悉呈各位桐乡读者,希望能作为大家观察历史真相的些许参考之用。
, C9 k9 L0 f" w1 b! @4 B) S 白梦女士的这篇文字,用作考证立论的立足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台湾高阳的相关“考证文字”,尤其在《清朝的皇帝》一著中,所引尤多。高阳很明显是以“历史考证”来辅佐小说创作的成功典范之一,也是作家当中染有“考据癖”的重要代表之一。前一特征与今人二月河略相似,后一特征又与张爱玲、刘心武颇相类。在小说创作上,无论是高阳还是二月河,都因那前一类特征而大受其利;而在史实考证上,无论高、张亦或是刘,却都因为基本考证方法的错误,影响了整个考证的成果。这大约也是此三家终只能委身于“作家”名列,竟不可冠之以“学者”名衔的一份主要原因吧。
; B5 j; t9 R. e9 d3 J9 d 由于这个条件前提,白梦女士在原文中引用的大量来自高阳的所谓“考据材料”,其可信度就已经要大打折扣。我们不急于否定白梦女士的论点,只单从高阳对于这一系列故事当中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考证”当中,就可以近乎很随意地抓满一大把错误与疏漏。我为了陈述的方便又避繁琐,只拣几处较具代表性的案例,来分别阐述高氏考证的谬误与粗疏处。
/ I2 K7 z4 K* ?3 s6 R 第一,“文头武脚”的取名是方、冒二家的事先约定吗?- w( `, |$ M; W: i( C) y
方拱乾有六子,取名皆依“文头武尾”法,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既知依据,这在多部清人笔记与正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如袁枚《子不语》、《清史稿》等,当为明证。然冒起宗为其子取名,果然是依“相约用文头武脚”的么?关于这一条,我曾刻意去查阅了相当部分的清人文献记载,并无记载。换句话来说,我至今得见此说的唯一来路,也就是高阳先生的《清朝的皇帝》了。不知道高先生这则说法,究竟有何明白的出处?或是自己的私家猜度?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即令我们真相信了冒襄、冒褒这兄弟俩的名字可以拿来作为“文头武尾”看来,那么冒起宗的另一个庶出子冒裔,为何高阳在这里只字不提呢?或许这位小说家不提他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冒裔之名,不能拿来作为“文头武脚”的有利证据,反而却成了这一臆测的不利证据了!& a* G8 _! m5 h, H5 D
事实上,给子女取名,在里面蕴含一层意思,是很正常不过的心理意识。就像今天还有许多家长为子女取名,仍然甚至带个“斌”字以示文武双全,方拱乾当年要用“文头武尾”法,也不过是为了寄托这层意思罢了。但方拱乾毕竟是个大读书人,不可能像一般人直用“斌”字这么俗套,于是他玩了一个文字技巧也就是“文头武尾”。但这个技巧明显不是与冒起宗一起商定好的,因为冒起宗没必要把自己前两个儿子都照套了这个技巧,反而到了第三个儿子就不这么坚持下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他“毁约”,也无所谓“相约”的问题了。冒襄与冒褒的名字让高阳凑到了又一对“文头武尾”,就开始自行擅说,明显只是为了迎合小说家天生的“无巧不成书”的心态。又恰恰就是这么一件真实的“巧合”事,竟让他折腾成一桩“预谋已久”的“地下情节”了。若要依此,我倒可以随意去另举一例来攀附一下了。就拿明末四公子当中,另有侯方域,其兄长取名各曰方岩(繁体巖)、方夏,是不是也要借着点变通的手段,认为是“文头武尾”了呢?事实上,无论是襄、褒、裔,亦或是岩(巖)、夏,都谈不上“武尾”。高阳只是拿着“襄”“褒”去硬凑,到了“裔”凑不上去的时候就干脆不提,这充其量只能算是“娱乐大众”式的编故事罢了。以其来证信史,只能称之为“小说手段”而已:够浪漫,却不够理智。
8 G' @# ?$ v. u8 a+ F8 n4 E% ` 当然,方、冒二家关系很好,这是固然肯定的。但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定要和方以智此系比较个胜负,都不能轻易下定结论。尤其不能在定论的依据中,拿出什么“文头武脚”的“相约”作为借口。高阳考证其大疏大失,由此可见矣。" m, q U9 V% i
第二,董小宛与董鄂妃果然是同一人吗?% P( p3 @/ K! L/ ~' B" Y% `
因为这一段是涉及到白梦女士陈述论点中几近一半的面积,所以固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又恰恰在这一点上,高阳近乎浪漫主义的小说手段,统摄了他的全部考证内容当中。而白梦女士在此节对于高阳的轻信,多少有些“盲目”处,以至影响到自己纠察历史的理性,甚至伤筋动骨。由于白梦在这一点上对于高阳的基本观点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方式,并未再在此基础有作任何补证与旁证,因此拙文在这里只能依据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与《高阳说诗》中的基本考证方法,来提出一二批评。$ q4 Q6 J0 M$ o* s6 A8 B: h1 B
高阳在董小宛与董鄂妃关系的“考证”上,是自称延续陈寅恪先生的“真传”的。但事实上这个说法完全行不通,甚至还带有一点借势拉拢与“自欺欺人”的嫌疑。小说家不能为写实而做“考证”,多半却为浪漫而做成了“索隐”。今人如刘心武者做成如此,稍前的高阳亦不例外。通看高阳在这一节上的“考证”,很明显根本就没有遵从考据学上所须遵从的逻辑,却是先入为主地去设定一个预期结论,然后围绕这个结论开始绕桩打转。这样的结果就是“强迫”了之前毫无关联的诸多案例,在一个“中心结论”下突然很莫名其妙地就联结到了一起。具体到高阳的“考证”细节当中,就是首先一马当先去插上一面旗帜,号称“董小宛=董鄂妃=端敬”,然后马上把端敬的所有有利资料都攀附上去,便欣欣然发现尽悉吻合了。这种方法能作为一种科学的考证手段么?当然不能。而其中暴露的各样滑稽无稽处,就在所难免。我在此仅举数例,足证其无端甚矣。
% s+ w# U$ D4 f8 h/ Z 其一,高阳推翻不了孟森《董小宛考》中的年龄悬殊这一最大关隘问题,便活活拖出一部《过墟志》来,硬要拿这个小说型的故事来例证出“董小宛三十三岁得承恩眷,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为了迎合高阳这个“莫须有”的可能,我们读者必须做出哪些信服呢?说得通白一点,就是要求大家都来相信,这位秦淮一代名妓年至33岁在清宫初蒙一位尚不满20的风流皇帝的专心爱宠,随后迅速升迁直至册立为皇贵妃大赦天下,最近不幸早逝又硬是让这个少年皇帝痛不欲生大办丧事精力憔悴、落到最后还追随芳魂远去……我们只能说这个故事编的确实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感人,但这个“莫须有”,是不是也太荒唐了一点?高阳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佐证,但事实上,即令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相信董小宛在影梅庵并未即死而是被掳北上,也根本不曾相信什么董小宛即董鄂妃说,并明称“小宛之非董鄂妃自不待言”。也许陈持此说,也是因为孟森先生《董小宛考》中所稳握的年龄一环节,已经无可推翻,又兼旁证何其深厚、岂是高阳几丝臆想可以推翻?
7 K* L9 [ C% \ 其二,高阳围绕自己预设的“核心结论”,然后开始在解释诗典的时候完全一厢情愿去做“索隐”,几乎全都有失偏颇。例如在解龚词《贺新郎》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要换一个思维路径,就丝毫没有不妥之处:“碧海青天”固然用义山诗典,但嫦娥飞天而去,可表天上人间阴阳悬隔再见无期,如何就如高阳所说解作董氏未死高高居于权上了呢?再如“破镜”典,更是羡前人可以重圆,而己身却已隔人世不得再有重逢日。何况若果如高阳所猜度,董氏入宫受宠也是在“佯死”的六年之后,一来龚写吊词如何能未卜先知?二来龚只是清廷官员又怎知后宫纳妃原委之大事?都不过后世江湖谣言,小说笔法,焉能受高阳先生如何大加索隐?再落到吴诗八绝句之前的小引对联“名留琬琰,迹寄丹青”,其中“琬琰”不过是溢美之辞,而高阳先生在这里非要激动起来大做文章,似乎只有“御制行状”“词臣诔文”才够得上“琬琰”之美誉,岂不怪哉?
% @! P9 }5 k1 g 其三,陈其年《妇人集》记董小宛事,有若干处未如高阳先生的“心意”去记载,便被高阳先生大做文章,以为有“隐笔深意”。其实陈其年记载,本为无心,不知道高阳先生用心机处为何如此深重?以平常心去翻阅《妇人集》,便知高阳举证,全不在理。《妇人集》记女子多未用全名直称,有何不妥?如记陈圆圆事,只记“圆圆”;记顾横波事,只记“顾夫人”;记柳如是事,只记“河东君”;记桐城方维仪事,亦只记“姚夫人”。难道这些人事都须有“隐笔深意”么?荒诞真不可推敲了。至于注者在文后称“姬后夭”,高阳更做大胆假设,以为是“恐被祸”之举,称“(小宛)二十七岁而殁,不得谓夭;端敬三十四岁而殁,更不得谓之夭”。然后古人早有称“年五十不称夭”,何故?明人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亦有记载一个叫做李逊的汴京举子,36岁的份上死了,题有一诗云“休为李君伤夭逝,四龄已可做颜回”,此又有何不可?若是依高阳意,此处注者有意用“夭”是要让诸者产生错觉以为董姬至死不过一个雏姬,则其前称嫁与冒推官,又居艳月楼集成《奁艳》,于情于理都不可以“雏姬”视之了吧?倘若之前的明提人物作注点可以“被祸”,那么这场祸,又怎可以因为“姬后夭”三字得幸免?
" b" c! e" ~4 u) Z* q 其四,高阳举证称关系端敬的册妃文与行状,均只言“董氏”而不言“董鄂氏”,是本姓原故。这是极大的无稽处,满人在入关之后,多改以汉姓,其中董鄂氏就有一部分改作董氏,在这里直呼“董氏”,难道也不可以?假如真的是因为本姓董而呼错,那就更不得了了:御制的册妃文与行状中,竟然都会犯下如此天大的错误?别说这文字不能用出来了,连错写的官员,都一定要犯杀头大罪呀。若这样的罪尚不及死,何必又有以后的那么多刻意“隐瞒”?满人入关后,不止在表面上将姓氏汉化,尤其注重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因此元、清两季相比,满人在民族文化大融化合成就更著。所以董鄂妃虽系满人,能够能晓汉文化,高阳先生大惊小怪以为“满洲从龙之臣,入关之初,本身尚多不谙汉语,何能教养出一完全汉化的女儿如端敬也者”,其实亦可参看清室礼亲王昭梿《啸亭杂隶》中一条记载:“近日之栋鄂氏,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为金时所迁,处居栋鄂,以地为氏。”此或栋鄂氏即董鄂氏。可见董鄂氏本源,为宋室后裔,则后人受家学影响,能够通晓较多的汉人文化,又不在情理之中么?或许,又恰恰是因为董鄂妃在入关之初的清宫中即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才使其在顺治帝面前更为招幸,以至连受恩宠,有清一代莫敢比肩。相比于高阳氏的牵强附会,不是更令人信服么?8 x* U! Y: V4 O- O) D
我不过是顺着高阳在《清朝的皇帝》立证思路中,逐条拣出重新分析,即知前四条基础立论处,全不成立。往后更多的衍变,同样逻辑混乱理智不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并举。从上可见,高阳明曰效法陈寅恪治学路径,其实迥然有异,这也是受学问所限而至。陈终可以冠之以“学者”“国学大师”之名号,而高阳终不过“作家”“小说大家”之头衔,这是在情理之中的。高阳在考证上的基本方法,就已经用错,仅为了圆满自己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意愿,开始将历史材料任意发挥,终至落此。相较之下,孟森与陈寅恪二公,于治学考证中何其严谨,绝非高阳可比。而高阳从错误道路中走出的错误结论,也是我们无法依从的了。据此,白梦女士因尽袭高阳说,在原文中所述凡与董小宛事件相关者,不再成立。7 `6 l# p2 `. @ c
第三,钱谦益等人降清的背后果然“另有图谋”吗?
: s/ a; e/ q2 B' l 我们不妨暂时抛开这一议题,只看白梦女士在原文中做出的一段“大胆假设”:董小宛入宫后,也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她施展手段,深得宠信,待产下皇子,顺治本要立为太子的,可惜四个月就死了,若此皇子长成,真的做了皇帝,那清朝的江山岂不血统不纯,岂不又回归汉族了?0 J \/ j! }/ G0 H' v% {
读到这里我难免有些错惊处,因为我在疑心自己当时究竟是在看篇历史述文,或是在看部古装影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大胆假设”,也只能存在于我时常提起的“电视剧情节”当中,是当真没有什么真实可依性的。假如说这样的“使命”有何其高明与可取处,当时汉人何必选送一个年已长龄的董小宛?是欺汉家无女或寡美色么?而且又何必只送董氏一人?既然真要靠这个产子立帝的方法来“还我河山”,那还不如用“乱枪打鸟”法,送上一批汉家美女入宫,个个都去邀宠于清帝,个个再都为清帝产子。我们汉人就不相信,这么多子嗣都会有“早折”的下场?只要有存活,就大大提升了立嗣的概率,汉人重收江山不就更是“指日可待”了么?事实上,这种情节的编造,本来就是无稽的。白梦女士以为这些汉族文人就是要力图“保护汉统”“使满清汉化”,其实这不需要这些汉人来做“远见”,因为清朝的帝王本来就有这番远见了。他们刚刚入关,就知道要想保证江山长久,就必须去努力学习利用汉人文化。于是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汉化”了,这就是清室皇帝相较于蒙古皇帝的高明之处,也是清室最终可以笼络汉族文人的原因所在。而且清室也从未拒绝过汉女入内,但帝王家似乎从来不怕这会导致什么“血统不纯”以至于“眼睁睁看着刚刚到手的江山还归汉人”。这只能说是小说手段,影视手段,不过娱乐大众罢了。' B: q5 T) @5 U7 g
再反思到钱谦益先降清后与起义有染的情节,我们就要据此以为钱氏当年降清一举,旨在为日后生事而设局么?决然不是。柳如是眼睁睁看着钱老头变节了没有去寻死,是因为她眼里不过鄙弃钱氏的操守,但不至于生念俱无,这完全是两码子事情。就像当年李清照也是热血沸腾的奇女子,但获知自己丈夫赵明诚在前线当了逃兵,也只是感觉羞辱而不至于蒙羞自尽罢?不过柳氏毕竟是个难得一见的烈女子,所以当日劝钱死节不果之后,竟真有“奋身欲沉池水中”的壮举,惜不遂。柳如是最终自缢,则是因为钱老头已经断气,自己在钱家却处处受排斥无法立足,这才是女人的正常心态。但钱谦益毕竟是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带点软骨的文人。他之前身为东林党领袖就已经退让了许多东林党人的气节,使得最后东林党竟成“藏污纳垢”之地,他的责任无可推卸。后来再顺应形势而降清,也在他的性格之内了。据《南明野史》所记,“钱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其实这种丑状,我想在降清一代文臣当中,可居“翘楚”了,恐怕是龚鼎孳等人尚且远不可及的。至于钱氏最后重又走上反清的道路,是因为文人骨子里又总会以“变节”为耻,事后追悔不及,更在情理之中。我们考察明清交接时期的诸多“变节”文人,诸如龚鼎孳、吴伟业、侯方域、施闰章等人的诗文,大抵多有同类的收获。这是文人矛盾痛苦中挣扎的一面侧影。如果换说之前的降清就是假借形势的“另有图谋”,其他诸如妻柳如是、侄金圣叹的嘲骂讽喻都不过跟随着“演戏”,那么这样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真骨气文人,最后所倾注的“图谋”竟然只按压在那几场根本不堪一击的所谓“起义”上,岂不可笑?再从钱谦益生平行状中,也不难知觉他的思想与立场改变历程,绝不至如白梦女士的浪漫式假想。此节有前辈诸公力证颇多,当不必赘述。陈寅恪先生对钱氏曾作过如此般评价:“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此解可谓颇具客观了。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