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0444
- 积分
- 18340
- 威望
- 14454
- 桐币
- 969
- 激情
- 10049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224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4-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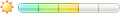
版主
  
- 积分
- 18340
 鲜花( 28)  鸡蛋( 7)
|

楼主 |
发表于 2011-10-2 09: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少年共产党
, i. p9 y7 x, o- f3 V) n+ ~: m& q) `" v F8 Q
' N& h6 {) Q. d
「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同他一样住在城里的,还有几个人,大部分是蒙达尔派的头头,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孟、汪泽巍;尹宽和王若飞来做工时也住在城里。他们倒不是为了工资更高,图舒服,而住在城里的,而是为了避免群众反对,不敢住到厂方免费供给的木棚宿舍。二十几个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里。那里不付房租,电费,水费。二个安徽学生,汪同祖和余中揖,脱产给大家烧饭,打扫,照顾财物。每人每日付饭费三佛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资在内,月底报告帐目。二人照领厂里的计时工资,即每日十佛郎。面包尽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此外有汤。我自从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以来,日常伙食没有这样好了。我做的始终是计时制,每日十佛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十小时,即一小时一个佛郎,帐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我每月净收入为二百四十佛郎。付出九十佛郎伙食费之后还剩下一百五十佛郎可供还债和零用。我没有做衣服,一直穿着香港做的三件头西装和初到法国买的现成大衣,内衣添制是另一回事。
1 k: _5 u% M+ \1 ?1 c/ s) _& q* Z" b! I) `4 S4 _% `
木棚里住的人,四川、安徽二省共占半数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余各省人更少。我只认识一个秦治谷,他在圣日耳曼中学读过书,我在那里认识他,同他说过话,似乎我去墨兰也是请他先租好房间的。他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里倒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却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来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对待我,向我谈社会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我很诧异,后来才明白他是从尹宽处知道我的。那时尹宽并不在蒙达尔,我不知道在甚么地方。李慰农——这个人就是李慰农——大概得到尹宽的信来注意我的。我渐渐知道他是安徽巢县人,在芜湖读书,同尹宽一起来法国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张圣日耳曼中学中国学生的集体照片,发现其中也有李慰农,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宽一起在那个中学读了半年书。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别的安徽学生也认识尹宽,但提起时都没有好感。他们对李慰农也没有好感,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尤其反对他爱谈社会主义。那些四川学生也反对谈社会主义,听到人家谈话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时候,就走开了,或者说「又是社会学!」我同李慰农接近,引起他们注意。
0 K6 p% {. E" C# C9 F' h3 u9 d, X. c( S4 i3 U2 U6 o
我一到木棚,就发现西南角靠墙的床铺上坐着一个老头子,带着眼镜。留着一部山羊须,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没有去工厂做工。秦治谷告诉我,他就是黄齐生。我知道黄齐生,他是汪颂鲁的先生;他带着一批学生从贵州出来在全国游历,去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名人,其中有康有为、章炳麟,也有陈独秀;他带着他们去过日本,又带着他们来英国和法国。他自称来欧洲考察教育,并不像徐特立(另一个老头子)那样标榜为来法国勤工俭学的。二八运动以后,里大运动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调人,奔走于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之间。《旅欧周刊》或勤工俭学生发表的文件记载此事。我想不到在这里遇着他。不知道甚么人安排他住在这个木棚里,在这里吃饭,不交伙食费,有时我们上工去,他帮助打扫,蒙达尔派头头没有一个人同他接触。
( `/ Q2 P$ h# S, Q0 \6 s( J7 _4 w, X8 l' Q3 a! T) B3 c
黄齐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细。他看见新来一个青年人,便同我谈话,掂掂斤两,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似乎当时别的人都不愿同他谈话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消几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细了,于是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关心我。他的思想还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阶段,对我不会有甚么帮助。9 b$ U+ z% R. X/ A+ k
1 v5 `& l% U( l6 h; \% O! K2 r
我当时尚未放弃考进大学的计划,尚以为来此做工是暂时的,一旦家里寄钱来又可恢复自学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时工以后,我还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到九点或十点以后上床睡觉。我还携带一本法文的解析几何,每日学习一点,以后才丢开了。
% r. I$ Q5 _ Y8 k1 Z' ~, }+ S* D* D/ w; m+ C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3]
! R6 @8 B9 A, U; K% R1 W0 h, Y2 x5 r7 p$ t
大概在那个时候新出版一个《工余》杂志,寄到蒙达尔木棚来,大家都可拿来看。过去只有《旅欧周刊》,在都尔的中文印刷厂铅印的,记载旅法侨民的消息,也有言论。那是华法教育会办的,没有人爱看。勤工俭学生有甚么事情就发表宣言、公启,用胶印印几十份散发。胶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买一张胶版纸,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写在一种特殊纸上,然后把写字的一面覆盖在胶版上,揭开以后留下墨迹,就可以用普通纸头去印了。我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看到胶印。勤工俭学生自己办的油印刊物,《工余》是第一个,我看了一两期,后发现它并不替华法教育会及其它统治者说话,于是投了一篇稿子,随便用一个笔名。不久注销来了,但有许多删节(以后知道是陈延年删节的)。木棚里的人纷纷议论这篇文章,猜想是谁写的。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写的,可是我听到李慰农低声告诉别人:是郑超麟写的。我很惊讶。现在想起来,并不奇怪,因为我同李慰农谈话发过这种议论。究竟甚么议论,用甚么题目,署甚么笔名,我都忘记了。如果有人收藏《工余》,我可能找出这篇文章。/ [3 z3 `5 q! [ Q4 E" @
8 b) y( r' n1 H5 f9 U# _! j 李慰农大概同尹宽一起早已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但他未去占领里大,未当代表,未出头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众不仇视他。仅仅为了他爱谈社会主义而当面挖苦他。至于住在城里那些头头,以及湖南籍的工学世界社分子当时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2 i6 N5 a9 b4 V# E6 f8 T H% ^' k, @, H- q
有一天,天气已经转暖了,李慰农暗中通知我:「明白,星期天下午,有人约你去森林里谈话。」我答应了。工厂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里,会见了李慰农,韩奇和薛世纶。约我们去谈话的,就是薛世纶。我早知道这个人,他是蒙达尔派的第四个头头,在工厂上下工时也有人指给我看。至于韩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没有同他谈过话,但秦治谷告诉我:这个人头脑很不简单。/ q2 \5 {5 H6 Z+ C8 b. ]& _% c
% P7 L. {# U+ E 我们在森林里坐下来。薛世纶说了很多话,结论是说:现在有人发起,要组织一个少年共产党,征求我们三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李慰农,不用说,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早已决定参加了的,但薛世纶还是把他当作征求的对象,同我们两人一样。我考虑了好久,才答应参加,韩奇比我考虑得更长久。如此,决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4 W( ^( N" g4 f/ K5 m2 x8 h
! D, I: N' y' A" A4 k 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事,是以张崧年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或其它名称)的决策,我事后就知道了,现在更有文件为证。据李隆郅回忆,一九二一年赵世炎在克鲁邹做工时曾写信给蔡和森建议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表示同意组织,但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名称;同年五、六月间(按:据贺果日记系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学世界社」开大会,李隆郅应邀列席,蔡和森提议组织「少年共产党」,但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李隆郅虽赞成,但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争论,故未通过。李隆郅这个回忆如果符合事实,那也可见,此时,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张崧年所说有赵世炎和陈公培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小组尚未存在,因为如果已经存在,赵世炎为甚么还要同蒙达尔派一起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会」呢?由此又可见。「少年共产党」虽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但名称已提出于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组织的显然是《人道报》上常见的 Jeunesse Communiste 而不是 Parti Communiste,即是团而不党。当时蔡和森不见得知道国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译名。赵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组织的,则是党而不是团,或者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党团的区分。以后,赵世炎同张崧年接了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工作便由旅欧支部担负起来了。支部派周恩来协助赵世炎进行这个工作。他们二人联名写信给住在蒙达尔的利瓦伊汉,不是直接邮寄的,而是托人转交的,约利瓦伊汉来巴黎一个小旅馆商谈建「党」事。时间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后,赵世炎就去北方县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达尔派函商建「党」问题。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信内还透露若干有关筹备的消息:蒙达尔派主张「工学世界社」全体参加,并「以去就争」;旅欧支部则主张个人参加;人数估计为法国约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若「工学世界社」坚持原意,人数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达尔派头头只说利瓦伊汉和薛世纶。但四月三十日给无名的信则说:「工学世界社世纶,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硕夫就是尹宽。可证此时尹宽是工学世界社一个重要头头,负责同赵世炎谈判的。赵世炎接着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可见,到四月三十日,双方争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五月一日,赵世炎就离开北方县到巴黎来,以后便完全为建「党」事而奔走了。
+ R4 g/ T$ Q$ u7 W0 U+ N4 c1 y+ s& O- c5 k7 |; j; @$ l1 ^, s, h
薛世纶约我们谈话,大概在五一赵世炎回巴黎以后,至早也在那个争执问题解决了以后。
: Z2 W4 T0 z2 ~- |( b- J! I( H& u" q4 V$ I( I8 e4 T
由赵世炎给无名二信,也可以知道建党事是设在德国的旅欧支部命令和督促赵世炎去做的。信内说:「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又说:「申府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这些话,对于那次在法国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尹宽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张崧年今天还活着,可是这段生活他几乎忘记干净了。他一九七七年回忆说:「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完全忘记了还有张伯简、谢寿康、萧子暲、熊雄!, T3 M$ I* a. T, r0 q9 u4 x/ D
" i; a. ]2 o4 _5 _$ V6 {6 m 森林谈话之后一个星期日,李慰农带我进城去会见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益、汪泽巍。似乎没有看见尹宽,可是次一个星期日尹宽又是在蒙达尔,因为那天我们四个人(利瓦伊汉、尹宽、李慰农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赵世炎到里昂车站接我们。我第二次看见他。我们乘地道电车到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去,到广场侧面一条不很热闹的街道 Rue Godfroy(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去。那就是赵世炎从北方县迁来巴黎后租住的旅馆。他住在底层,窗子开向一个小院子。我们当日就回蒙达尔去。谈了甚么话,我都忘记了,也忘记了有没有别的中国人同他住在这个旅馆。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我再去这个小旅馆时,几次都看到情况改变了:楼下的房间是陈延年兄弟居住,赵世炎则搬到二楼上一个房间,尚有其它五六个人也租住这个小旅馆,纷纷扰扰,热闹得很。我没有去别的房间,包含周恩来所住房间在内,因为大家都在楼下陈延年兄弟房间和二楼赵世炎房间会面。5 X5 W' ^, d7 O( |6 ]* B$ G
: {" T# T4 c) Z) }2 L2 Z- h+ i
4 G* P2 s, A9 L0 q*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