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1491
- 积分
- 245
- 威望
- 515
- 桐币
- 102
- 激情
- 4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53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6-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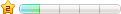
文都秀才

- 积分
- 245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08-10-6 10:5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方拱乾就是在如此恶风浊雨中,于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三日携家眷数十口由京师动身出塞的,此时,他已是六十四岁的皤然老翁。十二日后,抵山海关,他写下《何陋居集》(又名《出关集》)中的第一首诗《出塞送春归》: 7 H5 P6 Q) I/ W% D' f6 T4 A4 {
% x+ K3 Q2 Y% [( k1 G出塞送春归,心伤故国非。花应迷海气,雪尚恋征衣。* I5 x6 t+ m0 \+ v& u, h+ W4 T# |
! t. n4 V' ]9 r2 S6 Z/ r时序有还复,天心何忤违。攀条对杨柳,不独惜芳菲。; y" s1 r4 m5 S
# j# t* R8 T' y' B' |: e, P/ G; x
有怨怅,也有希望,但都是淡淡的,温柔敦厚味十足。大约他已意识到繁华逝水,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湛深的儒家后天修养则令他不愿逼视或者重视将要面对的“重冰积雪,非复世界”(《研堂见闻杂记》)的现实。在出关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方坦庵的心境都只如“市朝兴废寻常事,迁客何须问故乡”(《中后所城楼》)般显得略为凄冷苍凉而已,并且还有着咏古的勃勃兴趣。然而不久,他就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撕裂了。试读《温泉》:
# q; Z( w3 v [7 s) J
9 g7 t8 v) s# E* d2 R
& k! N; l; h( L+ N0 B, ~春风不散穷边雪,阳德长嘘北海源。自痛飞霜寒彻骨,逢泉喜得尚名温。
* W, M1 l2 Y7 \8 }' K8 D O* l' E1 [) g
/ u# {8 d! ^, ^9 [% d这时应已是送春迎夏的节候了,然而身在穷边,寒雪犹未消融,更难消融的该是心上“彻骨”的冷意罢?“逢泉喜得尚名温”,足见人间再无温情可以给迟暮老人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此后,他的心境更随着对绝域日复一日的深入灰暗下来了。《晤剩和尚》[6]云:“绪乱难宣说,无言不为禅”;《晤赤和尚》云:“嗟尔窜身来绝漠,闻予去路更蒙茸。”故人相逢,有体谅,有羞惭,有同病相怜,感情的双向摩荡是最易令人生感慨、生悲怆的。四月三日,坦庵写下苦中作乐、益形其苦的《生日》诗:7 t2 V5 z; r: [+ d- l6 J
4 D& y7 U8 Q# h E r2 k
不死头颅私怪天,奉兹严谴始惺然。欲留青海无穷地,令享红尘未了年。
' k) {1 ~4 @( L& j. N) W
1 s$ o# Q: c! j5 v( w- O* H岁月岂因殊域异,泡沤不受老僧怜。孩心对酒开涓滴,醉舞还同赤子颜。: R. |6 Q& f6 {" \4 b& N! a
% u# S6 }, o) P# I# ]/ O, k9 x! a
4 q3 e/ \8 a5 H& J6 o1 x怪话连篇,愤慨已难自制。更加怨而且怒的是《午日过年马河》:
* j$ w2 W/ w- m/ j6 g2 n
7 l! ]: ?: X7 A' Z- e$ C& c2 Y5 L `7 A6 p* j5 W3 X Y* M
信谗无一用,千古遂称冤。何与蛟龙事,空劳舟楫喧。8 H5 m% e" r }( | \! N
) F. C) ]- t( i; b命穷丝费续,天闭问无门。转觉汨罗浅,临流未敢言。
4 M3 t$ T8 o0 Z `- d/ A, s. u, L% t. o0 H3 H# Y
7 e' U- p, \3 M+ h$ ?3 |# D
句句写屈原,又句句关锁自己,而“蛟龙”、“天”、“汨罗”等意象又分明指向当今“至尊”,力度惊人。这样在特定时代、身世背景下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双关手法发挥到极致的好诗,没有科学的“知人论世”为前提,是真不容易读出味道来的。1 V5 X# u" M) u7 @
) i; o" L# s! }% L: W" o1 C
2 v+ { X6 d2 r) Z% v2 i& D
从懵懂宽怀到强作欢颜,再到愤懑难平,再到聊自解脱而时杂慨怨,这便是坦庵一路远徙绝塞的心路历程。七月十一日,他抵达戍所,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写下《宁古塔杂诗》百首。此后整整两年,他都是在以下诗篇反映出的复杂心态中度过的:; T! k/ I7 w1 r- e0 a/ @: d9 p
5 p5 T7 Q5 l3 _+ o
6 m6 ]) g- C: M& @/ G W已拼死道路,仍作里閈人。历险知天厚,偷生赖土淳。
' K- F) h& B! |4 s
, v9 s& p/ f* J9 A- p) r7 [
# s1 z3 @3 a6 G6 O* Q* L鸿伤无足慕,龙老不劳驯。翻笑桃源叟,多方苦避秦。(其四) 2 M. `% [9 u( v. |0 U+ D
3 k6 e" m' F0 t) i1 @. a
9 q* [: [( r9 `
心死身偏寿,形卑道更尊。(其七) & K8 d8 T* ^% C6 Q' u; R) @
; O" N- S3 G. I
边寒场圃晚,白露黍才登。碾钝晨炊晏,餐廉木椀增。
' T* N: j0 p' G- p+ o; d2 H& y7 U/ H; y# U/ k
! n Y5 h% Q$ e' q3 r3 ?( g提携劳瓮酱,荒蔓抱瓜藤。麻麦山中味,为农半似僧。(其十四) ( r5 O" X A- L |1 C
2 k. r5 b, ` f& r( L9 {1 \
; M- A0 h: o. ]$ K力困稻粱少,命从刀俎分。(其六十六) # p2 z* g8 |9 V! v" Q% y2 H
, k X8 c8 ]: {) a# l
率土宁非地,王臣岂有冤?愧无三字狱,空戴九重恩。
- S! {+ A1 Y) G7 J* @( C
% _$ J) y8 h# a2 A9 q6 D" h( \* H
1 P9 f" v2 y/ ?1 D3 J' u8 ~( ]5 u精卫高难问,豺狼远不喧。漫将哀乐事,轻向古人论。(其八十) 3 I. Y2 ^$ [, W$ k, w
" M* G: H" l1 Z, x; h: v9 t
前月已闻雁,今看带雨飞。不知何处去,敢问几时归?
7 H4 Y' n( n" x) J, o
. Q% o% a9 L* _: U- u
; m2 p1 @" o( @ s$ r) _( F伤重弓应贳,芦高食不肥。上林亦险地,系足且依违。(其九十)
, u1 c/ K* b7 J
4 |% `5 g( {9 s( L; O' L
5 s# I# k( W4 Y/ f9 R1 l毋论是强自排遣,抑或写农事入妙,又或牢骚沉痛,再或借物兴感,总之是有了悟道的意思,不再那么痴地抱着幻想或一味气苦了。然而正如随园赞赏的何南园诗云:“事到难图意转平”,心中的大悲苦并不因表现形态之多样而少减的。所以当顺治十八年(1661)冬月初一日、方得“召还”消息的第十三天,他在为编好的《何陋居集》写序时如此回顾了这一段生死寒苦的人生历程: 9 C7 g: }5 i! i& ]4 ]
/ i7 ]. ]( E" U9 c# x+ C }
屋不盈一笏,鸡毛笔杂牛马毛,磨稗子水作墨渖,乌乌抱膝,聊送居诸,不复料此生章句再入中华,流传士人口矣。昔人诵少陵诗,秦川以后更佳,殆谓其穷且老尔。余年较少陵入蜀时更老,若穷则不惟远迈少陵,既沈宋交欢,踪迹犹在舆图内。纵观史册,从未有六十六岁之老人率全家数十口颠连于万里无人之境犹得生入玉门者。咄咄怪事!
- y1 e% M. A) I 3 }; J5 X0 o/ h6 e; E- t
从其开阖顿挫的笔势看来,方坦庵的锐气实是并未因残酷的磨折而消减的。所谓“白头老子,崛强犹尔”,坦庵也未尝不以此自傲。他的“大节”自然不无可议,这一种以“崛强”对抗污浊现实的勇气则闪现出悲壮的人格光辉。
' J" R* Q; P+ a F6 K4 m: G/ }6 p! b
\, z+ q, Q A! u- {' c
顺治十八年以“认修前门楼工自赎赦归”是坦庵晚年的又一重大转捩点,然而他的心情却是“艰辛三载事,悲喜一言无”(《十月十八日得召还信》)。诚然,这不是悲伤事,可是以“莫须有”之罪流徙绝域,死里逃生,这难道又是喜事么?此种非悲非喜、亦悲亦喜、不能悲不能喜的尴尬心情,三百余年后走出“牛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想必都不会陌生。随之而来的,他此后的《甦庵》一集也就以更多的“超脱”代替了前一集中的凝重和感怆,因而耐读之篇少得多了。《前途闻虎警》一首尚有沧桑之慨:
* U! N* ]+ T9 W8 J" `5 A+ p2 R
/ N: m5 P+ W y; B+ M; j( ]) `+ a! M莫怪于菟啸晓风,劳生尽日畏途中。三年履尾浑无恙,不信人间有咥凶。
' \8 V& h A- c$ O" _( e
7 ?. c5 d3 i6 W8 e
+ s" q8 j3 w6 y6 r& W当然,从人性的角度言,我们不希望历尽风霜磨砺的老人再多一重自我的心灵刑罚。他的性情涵养决定了他不再那么激烈和痛苦,这是我们能够期待得到的最好结果。
; Q9 j- [2 y! r" N
& t0 j) f( v/ M$ n
) A% R6 O4 C7 Z/ a坦庵于本年冬月初启程南归,翌年正月入都,旋即南下,寓居淮阴,又改寓扬州。在扬州,他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南归后,坦庵在既老且贫、需卖字以存然而又颇矍铄峭劲的生涯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康熙五年(1666)病逝,门人私谥和宪先生。
" h$ f4 A6 N0 @; ^1 `, L( E7 z- h3 [; o% ]- M2 a d5 l
根据多种记载,坦庵生平诗作结有《白门》、《铁鞋》、《裕斋》、《出关》、《入关》诸集,然沈归愚辑《国朝诗别裁集》时已只言有《塞外》、《归国》二集,似自康熙末年其子孝标罹《南山集》案后(事详后文)已禁毁。至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时则似并此二集亦难觅,故此庞然巨帙中乃不收方拱乾其人。今幸得李兴盛等先生自复旦、上图所藏两种稀世版本中整理出《何陋居集》、《甦庵集》(即《出关》、《入关》、《塞外》、《归国》等集原名),并自《龙眠风雅》、《桐城方氏诗辑》搜遗求佚,于1992年出版了《方拱乾诗集》,俾使沉埋数百年的这一特殊诗人面目重为世所知。
5 `/ }2 j8 V q" H& u,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