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6289
- 积分
- 2595
- 威望
- 24024
- 桐币
- 6644
- 激情
- 1276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21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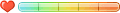
桐网嘉宾
 
- 积分
- 2595

 鲜花( 6)  鸡蛋( 0)
|
从枞网陈靖先生的《布衣鸿儒方学渐》,到桐网不平则鸣的《只有三个字是原创的论文》,无疑拉开了桐枞关于历史人文争纷的又一场瓜葛。维持了并不算长的时间,这场争论已经趋地平静。然而,事情的本身并不发于一种偶然。桐城与枞阳两地的地理行政区划,以及文化渊源的由来,注定了这些争纷与纠议的必然性。对于这一场争论,笔者差不多是一个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身份。说是局外人,是因为争论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我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野来“坐观”的;说是局内人,是因为我本来就属于一个地道的桐城人,再加上后一段时间还是简单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所以在这个身份前提之下,我只想用自己粗浅的思维能力,对事件的前前后后作一些总结综述性地表达。一非充当“和事佬”,二非充当“终结者”,只是个人的一些杂乱的拾起,再尽可能客观地做一定的申述建议。如此则已。为了表述的层面性,我考虑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J" o: v' f+ ?6 `. r+ n
! F' i3 J6 G+ R' Q一、方学渐与桐川会馆的争议始末及其总结7 k) i0 G* p( q9 e' j* A
此争议在网络上的源起,大约来自于枞阳友人陈靖先生的《布衣鸿儒方学渐》一文。文中所云诸种,皆以方学渐为枞阳人且于枞阳开创桐川会馆为前提。因此引发了桐城网与枞阳网两方面人文版对于此事的巨大争议。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名词叫做“各为其主”,发挥到这里便是“各为其乡”了。名人名物,自然要往自己的县乡拉拢,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将这种“常情”带入比较认真严肃的讨论之中,似乎并不合适。陈靖兄在桐枞人文方面的造诣,是我所熟知并向有敬佩的。笔者在这里如果侥幸可得以“朋友”的身份来与陈靖兄作若干商榷,那么我便想在这里就陈靖兄的原版文字作一二试论:+ z9 D$ y* t( s' }! F
其一,就是我在读陈靖兄本文的第一感觉,就以为本文不是拿来“讨论问题”,而是拿来“普及知识”的。如何有此说法呢?从行文的形式上,尽管陈靖兄惟其开阔之视野,对方学渐先生行迹种种,侃侃道来。然而可惜的是,这篇并不算作局短的原文中几乎无一征引处。诚然,陈靖兄在文末标注参考文献凡九种,可供讨论者搜寻探究。然而,从何处得何见解,在“论点”与“论据”之间,让人无法寻到一条明晰的连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家有心去卖力搜寻各种罗列资料,但苦于原有论证无线可寻,甚至在讨论的一开始,几乎感觉到“无从下手”。这不是因为陈靖兄的文章观点已经十分之完善而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恰只是因为原文论述脉络不明,无从驳难而已。所以,也正如陈靖兄交代本文创作原意时所表述的那样,实是“为《枞阳历史文化名人》一书而作”,因此只有“普及知识”的功用,而拿来作为话题讨论,似有为难了。我诚然相信陈靖兄的文字,不会来自一己私意的纯然杜撰,然而凡论述皆须做到言必有据,立必有信,这也是桐城学派著书立说的一贯传统,至今尚不可丢,更不该丢。. r) S3 m5 \3 Q; M" E) E8 S
其二,在陈靖兄初至桐网答复《只有三个字是原创的论文》这篇质疑帖时,曾有过这样的自我表态:“方学渐是枞阳人还是桐城人,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讲究依据,在目前依据不是太明朗的情况下,说是桐城人或枞阳人皆无可厚非。”这种说法在我这样一个迂腐学子看来,似乎是学问态度上的不妥了。有什么证据做什么结论,是我一直以为不可鄙弃的学问精神,如果在没有可靠的直接依据或推理逻辑之前,我们宁愿舍弃一种观点的立论,这是无据不立的态度;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只是在某个文献中找到一份完全孤立的信据,我们也宁愿采用“不取”的态度,这则叫作“孤证不立”。胡适之先生也正是以此为藉,在古史辨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阶段说”,提出要将中国可考的古史年代先“缩短”后“拉长”,前人如此,耐人寻味。在原篇文字中,陈靖兄既然已经肯定“目前依据不是太明朗”的基本前提,当然不能以略嫌侥幸的心态认定“说是桐城人或枞阳人皆无可厚非”,这让人感觉有些“蛮横”和“不讲道理”的嫌疑了。既然本着这样的心态,然后再如陈靖兄本人在枞网中所言“恭请网友指正”,岂不是多此一举了?最起码,是在不能下任何立论的时候下定了某个结论,而原作者又首肯了这种方法的可用性。所以,如果忽略错别字审查或病句修改关键词润色一类的编辑问题,这其中的“指正”必是无从谈起的。% b7 D( U, k6 [9 P7 Q. K
上面两条,事实上都是从原作者的立论态度上来做的阐述。我信任陈靖兄的学问涵养与学问精神,然而仅就此文而言,我只能抱以“否定大于肯定的态度”,来向陈靖兄阐述一二。无论是古希腊的亚历士多德面对柏拉图,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之面对蔡元培,他们在否定对方的同时都重复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说法;那么今天允许我不自量力地面对陈靖兄,私改成“吾爱吾友,吾更爱考据”,谨心奉献之。
. @1 R: y; w8 t% K; N 再其三,舍此二节,我们再看大家对于这场争议的核心问题所做出的讨论结果。我几乎只是一个旁观人,这里借助了前面各位先后展示的资料论述,不能一一细提,只能略加并举而已。这里相执的两大问题,我且来罗举如下:
% _$ h' h$ `! z6 f' W% ?& u0 U 首先,桐川会馆的地理归属问题。陈靖兄在原文中称“学渐以布衣主文坛讲席20余年,并筑桐川会馆于枞阳”,已经断言在今枞阳县内,其具体来由,如前所述并未细明。那么,我们从现在已经出示的所有举证来看,果真如此么?
3 `% R- x( j3 u! N5 m' | 方大镇《续置会馆颠末纪》文中曾有述及桐川会馆的位置:“西界祠后天井中心,东界河,南界旧馆,北界祝氏,风火及墙之址各不紊,是以续纪以垂后来。”诚如几位朋友的指谬,既然此中已有“东界河”的说法,而枞阳县城镇东无河的地理形势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东界河”的先决条件。3 l% A% P2 @2 y
随后,我又在明人焦竑的《澹然集》中找到了几位网友期待的《桐川会馆记》并曾全文发出。由于我本人几乎是个天生的地理白痴,当时以为这则资料作用甚浅,结果在同安闲人的帮助下才意识到它的重要可据性。它在地理位置上的表述语句很短,仅“馆负城临流,据一方之胜”一句。然而其中有说“负城”,无疑是说明会馆必在县城之内,“临流”再与前一条记录遥相呼应,双证并下,已可从中断定桐川会馆实在今桐城境内无疑。$ U& h" M, z3 d: A+ t( R
而情况还不止如此。诚如我在一开始的引文发见中所述,焦竑记录中的另外一句“自是东之枞川,西之陡冈,精舍相望,而一以桐川为宗”,似乎更值得我们思考。从这句话中我们至少可以捕捉到两个信息:第一,所谓“东之枞川”,显然是以桐川会馆为中心,而枞川在其东侧,足证其位属归桐城;第二,原文将“枞川”与“桐川”作为并列等次的两个地名并提,可见作者至少在撰写此文中,心里很清楚这两处的位置差异,而枞川“以桐川为宗”,恰恰证明了“桐川会馆”的地名由来,并不是所谓的某个时间段的“广义”上的桐枞合境,而根本就是切切实实的桐城境内。
# X$ A, K3 l) d# C& A* v0 S! _ 因此,据前文诸种所述,桐川会馆址在今桐城境内,断无可疑。而我们再需要探讨的第二大问题,即是方学渐究竟是“桐城人”,还是“枞阳人”。7 T3 |* H ]# ?) _* R, g" h. B
我个人对桐城的家族谱系,关注颇少,原以为此话题甚难把握。结果临时询问同安闲人,得知桂林方氏宗祠竟然就在桐城境内北大街内,使我不得不重新以为,本话题几乎无可争论。诚如我在曾经的《关于曹雪芹祖籍沈阳说的若干阐疑》拙文开头讨论的“祖籍”定义一样,改用其它任何不易固定的信息作为“祖籍”的判定标准,都是不可靠的,而最合理的判定方法,就是谱系宗祠。这大约也是李白至今仍被我们看作中国人而不是吉尔吉斯斯坦窜入中国的移民,以及方苞自行认祖桐城并被我们心安理得奉为桐城派之祖的根本原因吧?
, J9 U& Y% q ~6 _ 如若不然,有人要提出异议。那么,好,请在异议的同时提出一个新的可以统一的判定法则来?比较拿得出来的,无非是祖籍宗祠、出生地和墓葬地。我们能依出生地么?当然不能,如果这样的话,正如前例所说,李白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名人了,而方苞也就是勿庸置疑江苏六合人氏,他后来自称“龙眠方苞”简直就是不学礼义的“叛逆”之举了。那么改用墓葬地?更不妥,不信大家可以数一数我们桐枞有多少巨望族人因为各种原因皆是客葬他乡?难道我们白白认栽去主动把他们排除在“桐城人”之外么?所以,我们只能循着这个最传统不过的方式,确定方学渐了,以及整个桂林方氏族人,都应该划归在“桐城人”并且是“今桐城人”的范畴之内。% }, i# Q1 \( n! b5 {1 q) e
站在这个角度来返回到之前的争议话题中,一切因果是非都可以尽入眼中。我们小心谨慎得出的最后结论,正是方学渐和他的桐川会馆,完全归属桐城,毋论从前、还是现今。( k$ O, m. d: d& X* f
8 [: R; [& D! `[ 本帖最后由 觞客子 于 2009-2-25 18:07 编辑 ]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