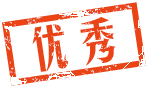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孙翔蔚 于 2018-5-9 12:41 编辑
小巷子的童年
我的小巷子就在桐城市和平路上第51号,长不过百米,住户不超过十家。我不知道这条小巷叫什么名字,擅自就叫她“我的小巷”吧。巷子六角砖铺路,一排高大的商住楼房成了她的一面围墙,三二辆停放的小轿车显示出小巷子居民的富足生活,一株不知何年何月自生的香樟树,凌空展开着他的绿臂,像一个卫士一般守护者小巷的居民。巷口那个出售刀剪、扫把、绳索、小农具的摊位仍秉承着他们的祖业。
把时光的焦距调制到四十多年前,总能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扎着两个雀尾,穿着干干净净的小花衣,脖子上永远套着一串钥匙,每天就在那巷子口打打沙包、跳跳房子(一种游戏),或蹲在地上看看小蚂蚁或什么都不干,就在那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巷子的居民对她都不陌生,过来过去都逗逗她:春儿,今天数了几辆车子啦?春儿,来来,我家有好吃的,我带你去我家吧?春儿,还在这里玩,你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吗?
是的,是的,今天的活儿还没干呢!然后就蹦蹦跳跳,晃着头上的小雀尾,胸前的一串钥匙一嗒一嗒地就跑回巷子回家了,干起活来:把每天家里煮饭米里面的沙子挑出来(那时候米里是有沙子的),小小的人儿干活可认真了,要是那时候数数能数到几千几万的话,她一定知道家里每天煮饭需要多少粒米的精确数。对了,您大概也猜到了,这个小姑娘就是我,小名:春儿。
四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因为身上长了一个小小的脓疮,在乡下的家里就医时消毒不全,感染成了“脓毒性的败血症”。母亲一路背着奄奄一息的我,急急赶到城里姨母家,连夜去当时的县医院抢救,好歹捡回了一条小命。此后姨母为了减轻自己独寡姐姐的负担和心痛幼小的侄女,就把我留在了身边,这一留,我就在姨母家生活了五年,也在小巷住了五年。
那个时候,县城可没有现在这般大,一条和平路上接汽车站下接老广场。最繁华的街道就是南门大街,麻石铺路,两旁大都是一层或两层的前店后住的铺面,小卖部、豆腐坊、早点店、裁缝铺、理发店比邻而居。与大街十字相交的环城路上,总是有一群用小铁环筐住石块,把石块锤打成小石子的大妈们。
每天早上,姨母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儿的早点店买几个朝笏牌包油条,顺带在豆腐坊打上一碗娇豆腐;实小城门口,菜农箩筐里那刚刚从地头采摘的、带着泥土露水的、青翠欲滴的蔬菜必须带几把回家。有一次看着姨母用一张钱买完菜后,人家还还回姨母好几张钱,我暗暗窃喜,拉着姨母快走,附在姨母耳边告诉她我发现的小秘密:(他们)为什么卖了自己菜,还要多给钱给人家?哈哈,把我的姨母笑出眼泪,一把抱住我:我的傻闺女啊,你也不看看这找回来的都是角票子呢……
就这么个傻傻的小姑娘,每天姨母上班去了,姐姐哥哥上学去了,就一个人守在小巷子口,在姨母允许的活动范围里到处溜达溜达。过了马路右拐就是“人民照相馆”,里面的摄影室里有为前来照相的人们准备了各种道具:书籍、军装、小洋伞、塑料花束、……一天下午,姐姐心血来潮,把我打扮一番,穿上漂亮的花连衣裙,头挽两个小发髻,扎上小红绸,脚穿一双小白鞋,肩扛着小洋伞,在摄影师毕师傅的照相机一声“咔擦”下,就把我小小美美的身影永恒定格。

巷子的正对面,那个时候是一家建筑材料铺,当然没有现在的瓷砖、木地板什么的,多是堆积着满屋的白石灰,每次车子下货的时候,就会扬起漫天的“白雾”,呛得人忙不迭地躲跑。铺子的右边也是一条小巷,巷口第一户人家有一个大大的院落,里面有一口井,姨母一家每天的用水就在这儿取,我常常就跟着姐姐后面进到院子里,记忆里一年四季这个院子总是春意盎然桃红李白,各种花儿我也叫不出名字,就知道夏天傍晚开得最艳的是“洗澡花”,墨青的茎托着那一朵朵粉红色的花蕊,像一个个正在奏乐的小喇叭,朵朵成簇,簇簇压枝底,我就专门收集那落在地上的一粒粒黑豆一样的花种子,总想着来年春天,自己也种上一株,到了“来年”自己总是忘了!
从我的小巷往左边走就是姨母上班的地方,桐城老橡胶厂,当年县里的龙头企业,三四栋的厂房围成一个大院子,每天厂里机器轰鸣,流水作业台上的工人有条不紊地娴熟操作着自己工序。拐角处的一栋厂房每天定时排放出一阵阵白烟,雾气缭绕。我就喜欢从那雾气里穿行,想象自己是那九霄天外的仙女(现在想想也许那就是工业废气,不知道当时我吸下了多少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啊)。
等到姨母下班后,我就牵着她的手,跟她一道回家,还帮忙做点小事儿,比如打酱油,出来巷口就有一个用铁皮围建的小卖部,日用百货样样齐全,店家用一个小小的竹制舀子从大泥钵里舀上一瓢酱油,像扯拉着一根长线一般就稳稳当当地就注入到带来的酱油瓶里,看得我是目不转睛,心里暗暗就发下了誓,长大后我也要学这样大的本领。
记忆里还发生过一件囧事,每天看姨母炒菜,快出锅的时候都会拿出一个小瓶子从里面洒一点点小粉子到菜里,然后我吃那菜的时候就觉得美味无比。那个从小瓶子里倒出来的东西像谜一样的吸引着我,有一天,趁着姨母不在家,我拿个小凳子垫着脚爬上灶台,找到那个小瓶子,偷偷地就往嘴里猛倒一口,想亲自尝尝那到底是有什么魔法的东西……结果?结果就是我长大以后再也不吃那叫做“味精”的调料!
姨母不上班的时候就带我在小城里逛逛,跟橡胶厂隔壁是“农资公司”,出售锅碗瓢盆、簸箕、扫帚、粪桶、粪瓢等各类农资物品,还代收各种破铜烂铁和皮草,收到的牛皮羊皮就铺在大街上晾晒,引来飞虫嗡嗡作响,膻气熏天。跨过脚下的皮草阵地,走过十字路口,左边就是“文化馆”,每年的元宵节,馆前的小广场上就会用毛竹扎起展台,上面挂满一盏盏身上贴着谜语的红灯笼,引来大批市民,或俯首沉思或轻捋髯须,绞尽脑汁地猜出一个而欢呼雀跃,小人儿也不知道对错就跟着拍手掌。
走过文化馆就到了“人民电影院”,拾阶而上,一个宽大的礼堂,一面巨大的幕布就是一面墙壁,一排排木制的长椅子都编着号,从后面小窗洞里射出一束光打在银幕上,银幕上人物就活了起来。一次,姨母带我去看当年大片《画皮》,那毛骨悚然的音乐、阴森恐怖的画面,小人儿看完,骨寒毛竖,出了电影院仍不知身在何处,抓着姨母的手回到家中,背靠着墙壁战战兢兢,变貌失色、呆若木鸡,姨母叫唤也不应声。那时那刻的感受,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无法忘却。
回到我的小巷子,往右走就到了县黄梅剧团,用毛竹扎制的篱笆大门在我当时看来如城墙般固若金汤,从篱笆的缝隙往里看,隐约传出那咿咿呀呀的黄梅小调,唱戏的角儿也都认识,那时候也没有“追星”这一说,要不,想要到他(她)们的签名也就一句话的事,就怕反而把他(她)们弄得“受宠若惊”。
再往前走就是农贸市场旧址,那时是成片的水芹菜田,泗水桥旁边的猪集上有欢叫的小猪仔,三八旅社的隔壁是木材加工厂,满院露天堆放的锯末散发出清清的、幽幽的泥土的芬芳味道。再往前走……不走了,小小的人儿走不动了,该回家了。
是的,该回家了。哥哥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完呢,从家里搬出一个小椅子到巷口,铺开小本子就开始写字了,先写“山、石、水、火、土”,再写“1、2、3、4、5”,一笔一划,端端正正,为的就是让走过来走过去的人看到我写的好,满口称赞或得个小糖果、小冰棒的奖励,让我小小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足!
这就是我的小巷,没有爬满墙头的蔷薇花,也没有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只有从墙外伸展入巷的几枝苦楝树桠给小巷带来片片绿意,但她给了我童年生活满满幸福的回忆。
离开她后四十年,我再也没有踏进过我的小巷,虽说我就住在小城,就住在她不远。每次从和平路上走,经过小巷时我都会转头往巷口看一会儿,恍惚间仿佛四十多年那个扎着两个雀尾,穿着干干净净的小花衣,脖子上永远套着一串钥匙的小姑娘还在那里蹦蹦跳跳,突然她也看见了我,用她那双清澈眼睛嫣然浅笑,似乎在问我:你现在过得好吗?是否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是的,今天我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如你所愿:我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最恬静的微笑,有最真挚的感觉,淡定从容,岁月静好!
一条普普通通的小巷子,四季更迭,岁月经年,婉约依旧,收藏着岁月的故事,等待着她的春儿姑娘: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